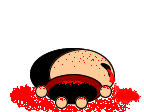二十四节气(春天写完了)
Posted: 2006-11-13 20:01
写个短篇系列吧,嘿嘿,没有压力,也没有坑不坑的说
楔子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之立春
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
梅红在二十三岁那年的立春上午,生了一个女儿:雪白粉嫩,可爱异常。
下午她婆婆来探访的时候,除了带例行的各种月子食品,还带了薄薄一叠春饼;尽着夸梅红这个时间挑得好:立春生女儿,万象更新,这姑娘势必活泼喜人。
梅红疲惫的倚着床微笑,女儿生下来以后她还没仔细看过,只依稀记得是红彤彤的脸蛋和手脚,肉乎乎的一团。
年轻到底占尽优势,梅红产假还没休完就已经恢复了从前的青春活力。百日抓周的时候,梅红穿着白底大花边的阔摆裙抱着女儿拍照,两张脸都眉目秀丽,比招贴画还要可人。
梅红想,这女儿还是生对了。当时意外怀孕的时候,她如何失措如何紧张,魏林和她如何左右摇摆权衡利弊;如今看来,生下来的决定,到底还是正确的。
梅红坚持要让女儿的小名叫立春。魏林拗不过,只好放得她满屋子“立春立春”的叫唤,只偶尔笑话她说,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屋里呆了个研究种庄稼的痴人,每天介埋故纸堆里研究节气。梅红对此报之一笑。
最后报户口的时候当然还是取了个大名,叫魏琦,写着绮丽,读着端庄。魏林揶揄梅红说,你一定懊悔没生个儿子,不然一定哭着喊着要给他取名叫魏无忌。
梅红没理他,把魏琦这个名字翻来覆去写了几遍,想想又在每个魏琦下面添上立春两个字,心满意足的笑了。
年轻夫妇,情意绵绵,又新添千金,旁人看着都替梅红甜蜜蜜。
立春三岁那年魏林觉得自己在北京的工作发展有限,白日里上班,晚上看书,翌年便申请了个国外的学校去读。走的时候他对梅红母女说,一定会快接她们过去。
梅红本欲阻拦,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让魏林去了:决心一旦下定,不在此时,便在彼时。
魏林一走就是两三年,最终把梅红母女都接出去以后,却跟她说,这两三年他在异乡寂寞无助,跟学校里的一个女同学相互扶持相互爱慕,已是难舍难分。
梅红震惊之下,脱口而出的第一个问题却是:“既然如此,你接我们母女过来做什么?直接回去签字不就好?”
魏林低头,“我觉得对不起你们俩,把你们接出来是我能为你们做的。签字的事儿可以等你找到学校或者别的什么身份以后再做。”
梅红简直啼笑皆非,想甩魏林一耳光却又伸不出手,只得愤愤的在屋里乱转。若是照她少女时代的脾气,这个时候她早就摔门而去;然而日下人生地不熟,女儿又还在屋里睡觉,她要走,也无处可去。
最终梅红还是留了下来,申请了一个跟她从前所学毫不相关的专业学着。
魏林还算长情,一手负责了梅红所有的学费,以及梅红读书期间她们母女的一半生活费。
梅红也不跟他客气,她的积蓄有限,再说,没有了爱,有钱也是好的。
她把魏琦的名字换掉,改叫梅立春。女儿已经半大不小,所幸这三年过的基本都是没有父亲的生活,并不觉得生活里没有了父亲,是多大的缺憾。
梅红飞快的读完了书,带着立春去了明尼阿波利斯工作。
立春在那所城市度过了她剩余的儿童时代,很习惯于冬天绵绵大雪,仿佛永无尽头的寒冷冰封。
梅红告诉她,她的生日,农历上说,是春天的开始:暖风始来,白日也会慢慢变长。
立春因此格外盼望自己的生日,甚至自做主张要把自己的名字改做Spring。梅红帮她到户籍处改了,只是,在家里依然管她叫立春。
立春每年假期到纽约魏林家里过几个礼拜,最初梅红还把她送过去,很快她就发现各大航空公司都有良好的托运小孩的服务,遂放心的把立春交给空姐们。
家庭变故时立春虽小,在后来的岁月里却也慢慢明白了事情始末。最初几年她还会回来跟梅红说有了一个小弟弟,渐渐的她再回到家对纽约之行已经缄默不语。
梅红并没注意,单身妈妈当久了,她的敏感细胞慢慢死亡。
一次立春从纽约回来,进了卧室又着急的扑出来说,“妈妈我拿错别人的行李了。”
梅红与她回屋去查看:果然,行李箱打开里面全是男子的衬衣领带。梅红赶紧合上箱子,却见箱子颜色样式都与立春之前带的显著不同,不禁略有薄怒,指责立春过分粗心。
立春正垂头丧气间,电话响了,是那位拿到立春一箱子少女装的倒霉人。
梅红道歉不迭,那人也不甚介意,只约了个时间地点交换箱子。梅红携立春前去,摁着她道歉。丢失箱子的是位中年男士,文质彬彬,姓方名端,看名字就似个谦谦君子。
他非常幽默有礼,说跟随自己多年的陈旧破烂儿,能跟立春的箱子搞混,十分荣幸。他且补充,为了这个难得可贵的巧合,能否请梅红母女共进晚餐。
那一年立春十二岁,亭亭玉立,人小鬼大,不等梅红犹豫就一口答应。
方端此人性格并不若名字迂腐,言谈有趣,一顿饭宾主尽欢。
梅红才得知原来方端公司总部在纽约,他在明尼阿波利斯和纽约之间,也是常来常往。他听说立春每年至少飞两次纽约,还遗憾的说,可惜没有早点儿被拿错行李。
饭后方端几番坚持要送梅红立春返回,都被梅红驳回,终于还是在饭店门口看着她们母女搭车远去。
立春十四岁的时候,梅红嫁给了方端,并随方端一起迁至纽约。
梅红到了纽约才意识到,她到美国那么多年,从未真正游历过纽约。这个城市,与魏林连接在一起,是她生命中一大伤疤。
立春在纽约的第一个生日,梅红给她买了春饼和烤鸭一起吃。立春吃得满嘴油乎乎的,眉眼都眯在一起。梅红心酸的发觉,立春整张脸,似从魏林的模样复印过来。
春暖花开以后,方端带着梅红逛纽约:鳞次比栉的高楼,呼啸的地铁,水波漾漾的哈德逊河,还有,标志性的自由女神像。
在前往自由女神像岛的轮渡上,梅红看到了魏林一家:魏林的父母,魏林和他后来的妻子,还有两个相差大约三四岁的男孩儿。
躲避已是不及,魏林的母亲先看到了梅红,微微点头示意。魏林见状回过头来也看到了梅红,犹豫一会儿,撇下家人走了过来。
这是数年来梅红和魏林首次见面。
魏林拨开人群向她走过来的时候,梅红突然想起,很多年前,他俩谈恋爱的时候,原是在自由女神像下合影过的。只不过,那是在北京的世界公园,自由女神像在那儿是水池里一个小小的微缩雕像。
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
正感慨间,魏林已经到了面前。方端握住梅红的手,冲魏林微微点头。
梅红神色如常的介绍魏林给方端,方端给魏林。两位男士握手寒暄,交换名片,然后又客气道别。
梅红耸肩,拉着方端要往另一边去。方端却捉住她说,“梅红我有件事儿要坦白。”
梅红抬头,满脸问号。
方端说,“那次立春拿错我的行李,其实,是我们故意安排的。我俩在飞机上飞来飞去碰到过两三次,她主动搭讪我,问我是否有妻室,是否愿意结识她的妈妈。”
梅红大笑,“立春早就告诉我了。不然以立春的糊涂,怎可能记得在行李箱上拴着家里号码的标签。”
方端握住她的手,意在言外的说,“我觉得立春开始我才觉得冬天原来那么长,她叫这个名字再好不过。”
梅红轻轻抱住方端,脸埋在他怀里,“是。我也这么想。”
春天的纽约,天高云淡,哈德逊河映着如洗的天色,泛着一片碧蓝。
人来人往的渡轮上,无数对夫妻情侣,在春天微寒的风中,静静拥抱着,看河中骄傲的自由女神像,慢慢逼近。
梅红与方端,也是其中一对。
之雨水
桃始花,食庚鸣,鹰化为鸠。
前往自由女神像岛的渡轮上,无数对夫妻情侣,静静拥抱。船上气氛温柔和暖,把纽约早春的彻寒,软软融化。
哈德逊河两岸仍有残冰败雪,天空碧蓝如洗。
这是二月末,春寒料峭。
秦欢一个人站在船边,看着河水翻卷上来打着船身,又带着灰白退去,没一会儿,露在外面的耳朵就冻得麻木。
船经过自由女神像岛的时候,停下来放人。
秦欢跟着人流走下来,看看手机,是美国的东部时间下午四点;在北京,应该是凌晨五点。林墨,应该还没醒吧。
她找到背风的地方,拨了长长一串儿数字,电话只响了一声,便听到林墨闷闷的声音问“谁呀?”
秦欢笑,“早啊,墨子。”
林墨叹口气,“哎,欢花儿,猜也知道是你。这年头,没人在这点儿给人电话。什么事儿?”
秦欢嘴上说,“没事儿,就想扰你清梦,”心里却悄悄补充一句,“今天是雨水,墨子。你还记得吗?”
仿佛回答她心里的这句话,林墨在那边说,“今天是雨水了吧?我上个礼拜看了看日历,想着你说不定会打电话来。”
雨水这个节气,对于秦欢,一直别有意义:十四年前的雨水那天,十五岁的她,初见林墨。
那也是个晴天,过完寒假后的第一个礼拜。
班主任从外面带进一个个子高高的男孩,跟大家说,“这是林墨,这个学期开始在我们班学习。”然后就把林墨安插在秦欢的旁边坐。
这是最最老套的一种开始:将近三年的同窗与同桌,两人都是老师的掌心肉;一起被开小灶;一起参加各种竞赛;一起上台领奖;也一齐背地里狠狠咒骂可恶的考试比赛课本作业周而复始。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平常的起头;他们之间,才永无以后。
其实并不是从没绮丽过:大学以后,两人因为在同一座城市,林墨几乎每天到秦欢宿舍楼下报道。两人还没拉上手,秦欢宿舍的姑娘们都已经自觉自发的管林墨叫秦欢家那位。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吧,两人开始每年庆祝雨水这天。
秦欢说,“这不大不小,也是个节气,是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日子。”林墨就在旁边配合的笑,然后两人就手拉手到小南门外的川菜馆子吃饭:一道京酱肉丝,一道蚂蚁上树,一道鱼香肉丝,还有给林墨的两瓶燕京啤酒。
两人总是吃得满头冒热气的出门;然后晃悠悠走一趟校园;再然后在秦欢宿舍楼下不依不舍的上演一场生离死别戏;最后秦欢伴着楼长每夜例行的“姑娘们,回来了,明天还见呢”的叫唤声,频频回顾着进楼。
这样一晃便是四年。
秦欢原以为和林墨会这样天长地久,相依相偎。
人世间不如意十之八九,可与人说无一二。
争端的开始是因为毕业:对于校园里你侬我侬的鸳鸯,毕业是一场大限:情深绵绵的,干柴烈火的,统统逃不过这一波未卜的未来。
那年的雨水,秦欢记得,是他俩最后一个一起度过的纪念日。
学期开始不久林墨便签了之前谈好一个公司,不料不几日却被告知工作前半年便要外派海外。他来与秦欢商量,能否一毕业就结婚,外派的时候便好申请秦欢一起。
秦欢怎肯愿意,大好青春大好年华,想象中毕业的时候正要大展拳脚。她且说,“何况,你签下这公司的时候,并未与我商量,可见你心中也没有我,谈什么婚,论什么嫁!”
若干年后秦欢回想那夜,总觉得事情本来可以完全不同。然而少年时候怎能知道,彼时真是嘴唯恐不利;心里受挫,愈发要在嘴上讨回来,势必要两人一起鲜血淋淋方能结束。
就这样两人开始冷战。
是时正好秦欢的论文导师谈下来一个海外项目,那边的学校说可以接收一个学生。
秦欢赌气想,“只有你能去海外吗”,遂草草答应导师,迅速补上各种材料,没一个月就收到奖学金录取通知书,然后开始兵荒马乱的护照体检签证。
忙碌的时候时间过得飞快,等林墨终于知道秦欢的去向,已是夏初:一切,已成定局。
秦欢签证成功,被BBS上认识的签友们拉去吃吃喝喝。满座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她却暗暗心惊:这一条路,再回不了头了吗?
晚上回来,秦欢远远便看到林墨坐在她宿舍楼下的花坛边等。昏黄的路灯把他的影子投在花坛上,折了一折,铺在地上一片暧昧的灰暗。
秦欢心里怦怦直跳,一边佯似镇静的走过去,一边在心里对自己说,“如果他开口留我,如果他让我别走,我一定留下来,再怎么样折腾也不怕。”
然而林墨没有。
林墨也有自己的骄傲:他是来告别的,他来祝秦欢一切顺利学业有成一路平安,然后说希望以后仍然是朋友。
秦欢听到自己微笑说谢谢,然后说很顺利,签证已经拿下来,家里已经在准备行装,还有,“当然,我们当然还是好朋友,墨子”。
那之后林墨再没有到秦欢的宿舍找过她。
秦欢出国之前,高中班同学聚会,两人才又见面。两人神情平静的碰杯,秦欢说“墨子一切顺利”,林墨说“欢花儿你也一切顺利。”
然后又是若干年。
秦欢顺利的拿到学位,签了一个可以四处游历的公司,一路勤勤勉勉的工作,职位稳定缓慢的上升。
她真的和林墨继续做着朋友:不远不近,不亲不疏。
她知道林墨毕业后如约进了那家公司,外派了;回去了;然后升职了;又外派了;又回去了。
并且,秦欢辗转从以前同学哪儿听来,林墨交了论及婚嫁的女朋友,然而不知为何又崩了。
她还知道,林墨的工作,也经常全球天南海北的飞;有些时候,她与林墨两人竟然前脚后脚的到了同一个城市,又前脚后脚的离开。
只是,他们总是相互知道得太迟。总是回到家里以后,打开网络对话,才知道彼此曾经前后几天,走在同一片天空下,甚至,走过同一家商店,看过同一场游行。
是哪里出了错呢,秦欢想,为什么,那么广大的世界,他们被送到同一个地方,却没有遇见。小说里不是常有撼动人心的重逢吗:在陌生的城市,陌生的街角,一举目,一转头,便看进对方的眼睛里,天荒地老。
难道他们的缘分,只得那么多而已。
秦欢二十九岁那年的立春,与同事一起参加公司里老好方端女儿的生日宴会。
那姑娘十五岁,粉红脸颊笑起来有深深酒窝。宴会完毕秦欢留下来帮忙收拾,旁听那姑娘与母亲娇嗔的对话,又是可爱又是可气,一时不觉怔忡:十五岁,那是她与林墨初识的岁数。
一转眼,已经那么多年;一切却还在原点:两人是朋友,也只是朋友。
入夏不久秦欢适逢公差回到从前读书的城市。
那并不是她第一次重返故里,却是第一次重游故地。
她摸索着找到从前跟林墨吃饭的地方。饭馆却是没有了,只有一条宽敞的马路,载着滚滚车流。
盛夏的下午,她孤零零的在路上走来走去,舍不得离开,却也找不到能坐下缅怀的地方。
一切都已太迟,她想。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然而命运却不这么想。
秦欢在路上来回走了几趟,失魂落魄的站到路牙边要打的,却有车猛地从中间换了两三条线别到路边,吱一声停下。
秦欢疑惑的低头,看到林墨在驾驶座上,对她微微一笑。
又过了两年,秦欢向公司请调,要求调回从前自己读书的城市,林墨也换了个不再满世界跑的职位。
秦欢和林墨认识后第十七年的雨水,他们结婚了:静悄悄的领了证,然后在一个小小的饭馆里,点了三个菜,两瓶啤酒;再然后,林墨一路开着车到从前秦欢的学校里,远远的停了,两人慢慢走到秦欢过去宿舍前的花坛。
那一带已经在一修再修下变得面目全非,周围却仍然围满了依依不舍道晚安的年轻情侣。
夜幕里没人注意秦欢和林墨这对不合时宜的中年人。
林墨就着黑握着秦欢的手,两人天南海北的闲聊,说从前一起去过却错过的城市与风景。他突然问秦欢,去过的地方,她最喜欢哪里。
秦欢笑笑而过,并不回答,很快岔过这个话题。
两人转了一小圈便自离开。秦欢抬头看路灯,这灯奇异的数年不变,连灯光都一样的昏暗。她看到脚下两人的影子拖得长长的,并在一起。
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地方,是你身边数尺方圆。
之惊蛰
獭祭鱼 鸿雁来 草木萌动
即使是接近午夜时分,大学的校门口依然人来人往,灯火辉煌。
苏涵就在这时稀时密的人流里,与秦欢林墨擦身而过。
是秦欢先看到的苏涵。
苏涵听到秦欢叫他,便停住,然后看到秦欢一身红衣,从树影间向她跑过来。待秦欢跑到面前,苏涵才说,“我收到你的邮件了,怎么,兜兜转转那么多年,还是回到林墨身边了?恭喜你啊!”
秦欢却不答,急急忙忙的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也不说一声?”
苏涵顾左右而言他,“怎么这么巧你们也来这儿故地重游?”
两三句寒暄的功夫,林墨已经走了过来。他冲苏涵点点头,揽住秦欢,“欢花儿,晚了,我们也该回去了,你让苏涵自己走走吧。”
苏涵感激他的细心,秦欢却不依不饶,问出了苏涵在这儿的联系方式方才离开。
苏涵看着他们并肩而去,却是没了再进这校园故地重游的心情。
两情相悦以后回来看旧时旧事,是要看流年变幻而人不变;自己这般,却是物换人非事事休,又有什么趣味。
他点了支烟,站在大门口。
便是这一支烟的时间里,苏涵想到,原来,今天是雨水,难怪秦欢林墨要选此时访此地。
雨水过后,便是惊蛰了。
苏涵原本并不是对节气敏感的人,然而大学里认识了秦欢,受了她的影响,不免对节气也注意起来。
苏涵是林墨的大学同学,因他而认识秦欢,跟秦欢却比跟林墨要亲近很多;归根到底,也是因为十年多前惊蛰那天吧。
秦欢那天原来是跟林墨约好了来找他的,结果因为出门晚了忙中出乱一头扎进苏涵的宿舍,迎面就撞见苏涵用刀在自己的手腕上划拉。
他记得秦欢貌似镇定的给他包扎好以后,揪着他说闲话,“苏涵,你知道吗,今天是惊蛰。节气上来说,今天的雷,是要惊醒蛰伏在地下的冬虫的。”
当时的自己漠不关心的笑了一下。
如今想来,确实讥讽,自己选来向喜欢的人出柜表白的那天,居然如此蕴涵深意。
苏涵踩灭了烟,伸手出来看了看:一晃十数年,当年留下的伤疤已经淡了,只有一片杂乱无章的白痕,自己多年来不离身戴着的手镯留在手腕上的印子,似乎倒还深些。
无论如何,苏涵想,他还是要感谢秦欢那天的匆忙,也感谢自己居然没有锁门。
很多事情,冲破了关口,回头再看,便是一片清明;只是当时,总是一片迷茫。
那之后是苏涵搬到了林墨所在的宿舍,与从前形影不离的朋友突然变成陌路。身边好奇和劝和的人,都一拨接着一拨,甚至一直到毕业散伙饭上,还有人劝酒。
没有人知道真相,苏涵不说,那个人当然更不会说。
直到大家各奔东西,只有秦欢,这个苏涵因缘际会交上的朋友,才知道始末。
真相其实简单,只是没人猜到:苏涵爱上他的朋友;而他的朋友听到表白以后对他避如蛇蝎。
同性恋,即使今天,在社会得到的接受程度尚且有限;何况是十数年前不知所以的大学男生。
后来苏涵飘洋过海,跟从前几乎所有的同学朋友都失散了联系。
一个人在异乡,仿佛是可以从头再来的。只是,走得再远再陌生,总归还是有想回来的一天。
人生长远,不能忘的,似乎总是起点。
那个起点,对苏涵来说,是多年前的惊蛰,惨烈的告白,和更加惨烈的绝望。
第二天苏涵果然接到秦欢电话,上来第一句话居然就是“苏涵你还是一个人?”
苏涵无可奈何,“秦欢,你新婚燕尔怎么不出去蜜月旅行,还在这儿耗着干吗?”
秦欢继续问他,“你是回来发展,还是只是探亲旅游。”
苏涵说是探亲,一两个礼拜以后就回去。
秦欢立即约了见面的时间,她说,“倘若你回来发展,来日方长,我们慢慢再见不迟;既然你马上要走,咱们这就见。”
他们约在雕刻时光,两层楼的新地方,新装潢:透亮的玻璃和宽敞的场地,再也没有从前的挤逼。
一杯咖啡,喝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苏涵也不得不放弃抵抗,答应秦欢的相亲。
秦欢得意洋洋,“我给你物色很久了,机缘巧合,也是最近才辗转从朋友那儿认识这个人,人家也是单身,也跟家里出了柜,我考察过了,无论才华相貌性格在同志里都算拔尖儿。”
苏涵到这会儿要苦笑也笑不出了,只叹口气说,“我对你们家林墨,真是充满敬意。”
秦欢态度强硬,拍拍他说,“我已经跟人家约好明天了,就这儿,下午三点。你没事儿吧?”
苏涵翻个白眼,“大姐,我说有事儿你能让我不来吗?”
秦欢点头,“很好,大姐我明天下午两点给你电话,免得你忘了。”
苏涵第二天如约到了雕刻时光,暗想,祖国大地还真风气开化,连同志相亲都遍地开花了。
这么想着,后来跟方礼桐把杯言欢的时候,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儿游戏心理。
方礼桐后来说,“咱们第一次见面,你怎么总是个神游太虚的表情,我哪儿入不了你的眼,让你目光游离神情可笑啊?”
那已经是数个月后在苏涵湾区的家里,方礼桐坐在苏涵床上,衣冠不整的翻阅苏涵过去的照片簿。
苏涵看着他,百思不得其解,“你这样的人,怎么会答应秦欢的相亲主意?”
方礼桐嘻皮笑脸,“我回去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秦欢把你吹得天上有地下无,我想见识见识,再不成也可以解决一夜。”
苏涵想也不想就把手里的东西砸出去,方礼桐顺手接住,给了另一个答案,“我看了我今年的星象书,说我红鸾星动,必有奇缘。然后我看到你手上样式古怪的手镯,觉得异人就是你了。”
苏涵懒得理他,方礼桐却在这时刻合上相本,正色说,“我其实是好奇。你知道,那天我跟我堂姐喝茶,因为是在她们公司的茶餐厅,那么巧就赶上秦欢坐在旁边。堂姐要把我掰直,一顿饭不断给我介绍她认识的适龄姑娘,我只好重申自己只爱男人,秦欢就从旁插口了,问了我半天,然后她就说她可以给我安排相亲,跟男人的。我拗不过她,又想摆脱堂姐,就答应了。”
苏涵揉揉额头,不错,这个原因最像真的。
方礼桐却看着他说,“我答应以后以为秦欢过段时间就忘了,不料没几天她就电话我订了时间地点。我去之前也觉得不可能是真的,天下那么大,哪里有那么巧,两个都在湾区呆着的中国同志,都挑了那一小段时间回去探亲,又赶上秦欢这样的人物给牵在一起。我看咱俩就该一块儿,想跑也跑不掉。”
苏涵嘴上一笑,说,“有什么稀罕,一半以上的海外中国同志都在湾区,那里面一半以上的人都挑春节过后回去探亲,避免拜年的麻烦。”
话虽如此说,苏涵也换到了床边,挨着方礼桐坐下,翻开照片簿给他说照片里的掌故。
方礼桐不久退掉自己的房子,搬来与苏涵同住;连苏涵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样一个蹊跷的起点,两人居然安定下去。
第二年苏涵和方礼桐联名给秦欢寄去一张庆祝结婚一周年的贺卡,落款的时候,方礼桐看苏涵落了个xx年雨水,好奇地说“想不到你对节气还有研究。”
苏涵放下笔,对方礼桐一笑,“是啊,雨水下来,是惊蛰。节气上来说,惊蛰那天的雷,是要惊醒蛰伏在地下的冬虫的。”
方礼桐瞪着苏涵,不知所以。
苏涵揉着左手腕上的手镯,戴得久了,这手镯竟如长在自己手上一般。他问方礼桐,“你知道我跟秦欢怎么认识的?”
方礼桐摇头。
苏涵继续说,“她先生林墨,是我大学同学,我大学的头两年,宿舍跟林墨的正好挨着。”
苏涵本来以为会讲很久,不料短短数句,就把前因后果全部交待明白。方礼桐听完很镇定,还拿来苏涵的相本,问他可有此人照片。
苏涵摇头,那仿佛已经是前生的事了。
十数日后便是惊蛰,苏涵回到家,发现方礼桐一个人坐在黑暗里。
他顺手拧开灯,问方礼桐“干吗啊你,一个人在家也不开灯?”
方礼桐走上来,一本正经地说,“苏涵同学,我爱你。”
苏涵平地打个冷颤,推开方礼桐,“神经病。”方礼桐笑起来,凑上来看苏涵的手腕,不等苏涵反应过来就拨了他的手镯,轻轻说,“已经看不见了。”
苏涵沉默的一笑,方礼桐继续说,“从今以后,惊蛰,就是我向你表白而且你欣然接受的日子。我们要每年庆祝,一直到老。”
苏涵这才醒悟过来,神色复杂的看向方礼桐。
后来秦欢致电苏涵,说,“你知道事情有多巧,如果那天我和林墨不是正好在那个点儿从你们学校出来,如果我那天在公司午餐选了另一张桌子,如果方礼桐的堂姐没有逼到他在茶餐厅表明同志身份,你们就见不着了。”秦欢叹口气,“真巧啊,我说你俩是缘分天注定。”
苏涵闷声说,“秦欢你是想说你自己是天吗?”
秦欢在哈哈大笑中挂了电话,正好方礼桐推门而入,说,“啊,原来你也在啊。我们公司安排了周末烧烤,要携带家属,我们一起去吧。”
苏涵微笑。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遇见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原来你也在这里。”
之春分
玄鸟至 雷乃发声 始电
湾区的春末夏初,空气中依然有雨的微潮,阳光却是暖洋洋的灿烂。苏涵跟方礼桐烧烤回来,吃得满嘴流油。
回到家门口,刚下车,看到一女子坐在台上,裹着厚厚的大衣,守着一具硕大的行李。
苏涵看看她,确认自己不认识;然后转头看方礼桐。只见方礼桐一脸牙痛的表情迎上去,嘴里说,“梓分你怎么来了?”
关梓分站起来,温婉平和,微微点头说,“家里出了点儿事儿,必须马上回去;但是我只能买到明天早上从三藩出发的机票,礼春说让我在这里叨扰一夜。”她目光从方礼桐换到苏涵身上,一脸抱歉,“对不起,礼桐哥,我以为礼春已经跟你说了。”
方礼桐还没开口,手机响起来,他掏出来看看,嘴里说,“嗯,他正要说。”,一边说一边接起电话,嘴里嗯嗯啊啊几句,然后说,“梓分在呢,要不要说话?”
关梓分站起来,正要走到方礼桐身边,方礼桐却又嗯了一声,挂了电话,嘴里讪讪的说,“礼春说,他会在南京接你,祝你一路平安。”
关梓分脸色明显黯淡了一下,继又礼貌的说,“打扰了,礼桐哥。”
方礼桐拍拍苏涵,对着关梓分说,“你们还没见过吧,苏涵,我的partner;”关梓分向苏涵微笑示意;方礼桐又指指关梓分,“关梓分,我弟的……”他支支吾吾半天,“那个,好朋友。”
三个人一起进了门,晚上安排好关梓分,苏涵靠着窗点了支烟看新到的杂志,方礼桐在旁看他,“你一点儿也不好奇啊?”
苏涵抬头,“什么啊?”方礼桐凑上去一起看他手里的杂志,“关梓分呗。”
苏涵笑笑,“有什么可好奇的,你弟的准女朋友?”方礼桐有气无力的挥挥手,“不,不是。哎,他俩一笔烂账;啊,不,更正,我弟一笔烂账。”
苏涵似笑非笑,“我看你就能看出来。”
关梓分怕误了飞机,第二天由方礼桐早早送到机场了,一飞十几个小时到了北京,关梓分连机场都没出,走了几圈,又换到飞往南京的登机口。
到了南京,方礼春果然在出口等着,一贯的风流劲儿,旁边不少女孩子走过都偷偷转头看。关梓分远远看到了,一阵疲惫。
正这会儿方礼春看到她了,殷勤的迎上来,接过她手里行李车,体贴的说,“坐飞机累了吧,你别着急,你外公目前情况还稳定。”
关梓分默默点头,由着方礼春把自己手里的东西接过去。
一路上关梓分都沉默着,由着方礼春喋喋不休的说话。最后她终于忍不住,敲敲前窗说,“礼春你安静一会儿吧,我头疼得很。”
方礼春立即住嘴,把关梓分送到她家。关梓分的母亲迎出来,老太太精神还行,看到方礼春还热情的招呼他进来,方礼春还没说话,关梓分已经打断她母亲,说,“妈,不用了,礼春还有别的事儿。”
方礼春见风使舵,赶紧附和,放下东西就走了。
关梓分走进自己的屋子,关上门,一路的疲倦如潮水般卷上来,她终于昏昏沉沉睡过去。
方礼春出来开着车,又接到方礼桐电话,嘴里哼哼哈哈的说,“嗯,接到了,知道了,哥你真罗嗦。”
方家跟关家毗邻而居,他和关梓分更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两人出生那天正好春分,于是一人分一个字:梓分先出生,挑了“分”字,他便轮到“春”。
这么些年两家若有似无的期待,以及梓分掩饰的热情,他都能感到看到。然而方礼春生就风流性子,再加上皮相上的倜傥劲儿,他并没有安定的心思,至少现在没有安定的心思。这些年他从来没有招惹过梓分,却也没有疏远过梓分。方礼桐屡屡教训他,“你若不喜欢人家姑娘,早点儿给人了断,别把人吊着,放也不放,吃也不吃。”他嘴上应着,行为却是依然故我。
二十余年的青梅竹马,方礼春相信梓分愿意等他,等他收心。
关梓分第二天早早就醒了,自告奋勇去火车站接姨妈。
南京火车站正对着阔大的玄武湖,清晨的太阳圆圆的一轮斜斜的挂,空气迷迷蒙蒙的,太阳的颜色也不甚新鲜:一切,都像截自一部陈旧的电影,带着将褪未褪的颜色,疲惫又执著。
结果火车晚点,关梓分一个人在车站等了又等,最后姨妈姨丈跟一个高个男子一起走出来,满面感激。
关梓分迎上去,才知道这一路火车甚多变故,时间交错,车中爆满,姨妈念叨,多亏这男子多有照料,才能平安顺利到达。关梓分谢了又谢,那男子虽然外表零乱容貌粗犷,为人却是谦和有礼,几人互相致意半天,才四散告别。
关梓分的外公没有平静很多天,就撒手西去。因老人聚过来的一家人,悲戚戚的办了丧事,又分头离去。
关梓分假期告罄,自己也收拾着预备回去。她公司年初把她外派到北美,说是半年既返,如今半年过去三个多月,自己又如此折腾一遍,时间也剩余不多。
走的那天是方礼春送她。关母经此不幸,精神甚差,但依然殷殷叮咛;方礼春也异常客气体贴,说是拿了假要把关梓分送到北京,请老人家放心等等。
关梓分与外公并不算亲近,然而生离死别总是大不幸,她一路沉默;方礼春也异常温柔,二十余年里少有的如恋人般的周到呵护。
关梓分上午到了北京机场,下午即要飞走;她无意问起方礼春什么时候返回南京,方礼春支支吾吾,说既然来了北京,顺便看看朋友云云。关梓分见状心中明白,也不再问。
飞回美国的航班依然热热闹闹的一机人,关梓分依然早早托运了在候机厅里等着,自行看书。不料坐了一会儿,有个男子过来招呼。关梓分看他半晌,心中默默回想,才意识到是那日在火车站接亲戚的时候遇到的热心人。
那人自我介绍叫山河,关梓分听他名字有趣,两人便有来有去的聊起来。
话匣一开,却发现两人居然兴趣相投,爱好类似。更巧者,山河便在关梓分所在的地方,也是进修外派,比关梓分更早半年,预定的结束时间却是相近。
两人一路回去,山河又把转机的班次换到与关梓分一致。二十余小时后两人抵达时,关梓分说话已经说得口干舌燥,然而内心却平静欢喜。
两人约了周末打球爬山,然后便一周一周持续下来。
山河关梓分都爱喝茶,也都挚爱普洱。两人周末运动完毕,总是在关梓分家消磨晚上。关梓分细细烧水洗壶,又将温水洗茶,最后做一壶普洱与山河分享。
关梓分用白瓷杯,山河用玻璃杯。上好的普洱,灯光下看犹如红酒,芳香醇厚。
两个月以后,山河的培训结束,关梓分的也是。山河把自己的东西统统收拾好运送回国以后,过来帮关梓分收拾。
关梓分开了门,伊赤脚站在地上,头发胡乱盘着,穿着工装吊带裤,手上戴着厚厚的橡胶手套,一脸疲倦。
山河笑起来,“怎么了,要回家了还一脸苦相。”
关梓分拼命挤出一丝笑来,“满屋子垃圾,扔也扔不得,留也留不得。”
两人在关梓分的屋子里收拾了一天又一夜,关梓分的屋子里的纸箱堆了半墙。末了她从橱柜里又抬出一个小纸盒,默默封胶。
山河笑起来,“还有什么宝贝,值得如此珍重。”话说完眼睛却瞟见盒子上小小的一行“礼春”字样,心中极悔,连忙住嘴。
方礼春此人,山河是知道的:平日里听关梓分说起不少,虽然没什么缠绵悱恻的故事,听起来往往让人默默叹气。
关梓分看山河一眼,把这小盒子放到方才有空的纸箱里,一边招呼山河过来帮忙封箱。山河过去,把箱子密密封好,握住关梓分的手,把她拥进怀里。
两人在那一周的周末离开美国。
方礼春仍然去南京机场接关梓分。关梓分与山河一同出来,看到方礼春微微而笑,把方礼春介绍给山河说“方礼春,我跟你说过的,我们家邻居,我们快三十年的青梅竹马。”
山河温和的笑,伸手与方礼春相握,“山河。”
关梓分在旁边补充一句,“我男朋友。”
第三年春分,关梓分新生的儿子满百天,她与山河把家中所有满满摆了一地,小家伙藕节一样的小手把每件都摸了一遍,最后抱了个小足球心满意足的玩了一天。
太阳落山时分关梓分的母亲把孩子接过去,山河便和关梓分出去吃饭。山河特地开车绕到南京火车站边,嘴里说,“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关梓分抿嘴,“我能不能不记得?你当时衣冠不整头发蓬乱,真正狼狈。”
山河大笑,伸手在关梓分头上胡乱弄。关梓分看看窗外,说,“山河你知道吗,今天是春分。春分乃半,今天是春天的正中间。”
山河眨眼,“我知道,这一天,在北半球昼夜等长,再往后天气渐热,白天渐长,夜晚变短。”
关梓分微微颔首,“是,白天越来越长,而晚上,会越来越短。”
这一天关梓分三十一岁,方礼春也是。
三十一年前,他们两人,一人在清晨出生;另一个,在夜晚。
之清明
苹始生 鸣鸠扶其羽 戴胜降于桑
江南的清明时节总是细雨绵绵,这一天是一年里公墓区人群最是稠密的一天。
关梓分与山河还有家中亲戚拜祭完外公,沿着山道缓缓拾级而下。迎面走上来一个一身黑衣的女子,面容秀丽凄切。经过关梓分的时候她不小心碰了梓分一下,本是最微不足道的一点儿轻撞,她却涕泪齐下的道歉起来。梓分不住地说没关系,担心地问她可好;她只掩面,匆匆忙忙踉踉跄跄的迈上去。
山河拉住了想跟过去的梓分,他说“到这儿来的人,多半都有伤心事。”
关梓分抬头看,满目是密密麻麻雪白的墓碑,一行一行,一列一列。她低头,与山河携手下山。
而那位撞了她的女子,却在这个时候停下了脚步,呆呆的看着梓分与山河并肩而去的背影。
只差那么一点儿,只差那么一点儿,常风,我们也可以是这样人人羡慕的恩爱夫妻。
她想起常风那天出门的时候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说“青青,我下午要开会,晚上会回来很晚。”她还记得自己听了这句话后的赌气,砰的砸上门进屋了。
那天是周日,常风出门以后就再没回来:他在家门口的街口被一辆闯红灯的车迎面撞上,当场毙命。
丁青青之后无数次的想,“我为什么要赌气,为什么不拉着他道别,也许,也许只差那么一秒钟,命运便会完全不同。”
然而人生不能重来,她在生的每一天,都必须为她那一天的赌气,不停懊恼痛悔。
这些年丁青青没有一日忘记常风出门的那一句话,和之后自己狠狠砸门的愤怒;以及,知道常风不在人世以后,她数月的痛彻心肺。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然而,毕竟也是活下来了。
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她的每一天并不比别人的长,她的每一年,一样只有三百六十五个黎明,三百六十五个黑夜。
这已经是她失去常风的第二个清明。
昔日粉红脸颊的少妇,如今只有苍白的脸色。她站在常风的墓前,久久不能离去:这石碑下,长眠着她的爱人,她本以为,可以相守一生的爱人。
舒平远远的站在这一列的墓碑边上看着丁青青。即使隔了十多米,他依然可以看到丁青青的悲戚,这个女子依然年轻,看上去却毫无生气。
他等了整整一个下午,夕阳西下的时候,丁青青终于动了动,离开了常风的墓碑。
舒平在丁青青经过的时候叫住她,他说“小姐,你掉东西了。”
丁青青茫然的回头,舒平说话事出突然,她完全不能理解他说什么。
舒平微微的顿首,索性换了句话,说“你好,我叫舒平,请问你怎么称呼。”
“丁青青。”墓园里的人总是思维缓慢缺乏警惕,丁青青未及细想已经说了自己的名字。
“丁小姐,这个时候天晚了,外出找车一定很困难,让我送你一程吧。”舒平用的是路边登徒子搭讪的话,然而在这肃穆的气氛里,从一身黑衣的他嘴里说出来,却不可疑。
丁青青并不防备,从两年多前起,她已经无所畏惧了。
两人并行下山,舒平小心的让着丁青青,又一路把她载到熟悉的饭馆,自作主张给她点了一碗粥。
丁青青看他,“舒先生,”她的语气很平静,“你不用费力气,我很好,我也没有意思认识新人。”
舒平微笑,并不回答,只示意丁青青喝粥。丁青青并不回绝,她已经过了拿腔作势的时代。
舒平在她对面坐着,看她喝完粥,才淡淡说,“丁青青,我可以叫你名字吧?”丁青青不置可否,舒平接着说,“你不必那么戒备,内人的墓与你先生的挨着,我已经连续两年在那儿碰上你了,你一直没注意过我而已。”
丁青青眉目缓和了一下,却也不说话。舒平继续,“内人去世已经四年了,你的这个过程,我也经历过,总以为自己再也活不下去了,以为自己……”
丁青青打断他的话,“我可以活下去,我已经活下来了。我只是不能再爱。”
舒平微笑,“你可以的,相信我。”
两人不再多说,只共同吃了这一顿饭,然后舒平便送丁青青回去。
丁青青第二天早上看到舒平等在她家楼下的时候,并不吃惊。
后来的日子,舒平有时出现,有时不;两人有时一起吃晚饭,有时不;周末的时候,两人有时一起出去,有时不。
共同的丧偶经历,让两人有心意相同的悲戚和谅解。他们心里都有一道墓;然而他们也都是芸芸众生里普通一员,需要呼吸,需要生活,需要陪伴,需要爱。
时间很快又是一年。
清明的时候丁青青又在墓园见到舒平。她比舒平到得早,特地看了看常风旁边的墓碑,果然有一座是舒平亡妻的,写着“爱妻林如好”,简简单单几行交待了生平,竟是癌症去世。
快中午的时候舒平来了,拿的是一束白百合。
丁青青想起来,这两年每次来都见到旁边的墓有白百合:大朵儿大朵儿的花,芳香洁净。
下山的时候舒平和丁青青一起离开。
那个清明是晴天,两人去了燕子矶。落日染得天边一片灿烂,山石依水,看下去真正半江瑟瑟半江红。
舒平说,“我和小好是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学,大学一毕业就结婚了,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我本来以为我们一定白头偕老。”
丁青青黯然,她原本也这么想。
“我们打算结婚两三年就先要个孩子,就在检查的时候,医生查出小好有宫颈癌,已经是晚期。从知道到她离开,不到一年时间。”舒平叹口气,“我亲眼看着她合上眼,我真不甘心啊。这世间那么多夫妻争吵着要分开,我们明明那么恩爱却不能在一起。”
丁青青伸手过去握住舒平,轻轻说,“情深不寿。”
舒平抹一把脸,“我没什么,其实这些年,慢慢的,我有点儿记不清楚小好的样子了。太久太久没有见面,我有时候回想过去的事儿,老要花很多时间想,她的眼睛是什么模样,鼻子呢,嘴呢,手呢。”
丁青青黯然,她也一样,时间久了,她只记得常风的温和,却渐渐忘了常风的样子。
丁青青说,“你知道吗,从医院出来那天,我站在台阶上看大街。那真是个奇怪的角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一天和平常没什么不同,只是一个普通的周日,车来车往,欢声笑语。而对于我,一切,却都不同了。”
舒平看丁青青一眼,紧紧握住她的手;丁青青回过神来,要挣开却不能,终于还是放手让他握了。
落日迅速的沉了下去,江面方才的波光粼粼也因之消逝;之前的半江鲜红灿烂,竟如一梦。丁青青和舒平并肩站立着,都深深一叹。
活下来的人,需要活下来的生活。再怎样光辉不能忘的过往,再怎么心如刀割的夜晚,时间久了,也就渐渐模糊。
再过一年,两人一同携手去墓园,共同拜祭了常风和林如好,又双双结伴离去。
清明过后,他们登记了。结婚那天丁青青穿一条珠光缎子裙,面颊粉红,微微带笑;舒平握着她的手拍照。拍完以后,两人审视一番,舒平揽过丁青青一吻,说,“真漂亮,非常漂亮。”
丁青青抬头看他,“我们会白头偕老吗?”
舒平心酸,“会的,我在路上一定好好看车,你也一定要按时检查身体。我们都会活很长,很久,很好。”
丁青青怔怔,舒平过去抚她的脸说,“来,笑一笑,今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丁青青拨开他的手,果然一笑,脸颊上浮起一对儿笑涡儿,绚烂如花。
活着,就一定会有新的开始:甜蜜也罢,苦楚也罢;活着,也一定能再爱,再痛,再流泪,再欢喜。
人生总在不停告别,不停出发。
两人并肩走出登记处,外面阳光很好,照得人暖暖和和,是南京晚春少有的大晴天。
之谷雨
桐始生 田鼠化为 虹始见
舒平和丁青青终究还是补了一场酒,请了两边亲密的朋友和家人,也有小小三桌。
那天恰好是谷雨,丁青青跟舒平挨桌敬酒的时候,一个年轻男人站起来,说“表姐新婚快乐!”。丁青青笑起来,拉着舒平说,“这我最亲的表弟,今儿还巧了,他就叫谷雨。”
旁边一个桌子的女孩子听了这话,扭过头来,打量了谷雨一下;谷雨低头看他,两人都颇为惊讶的“啊”了一声,谷雨想了一小会儿,说,“你是......夜猫”。
舒平听到这称呼,忍不住哈哈一笑,坐着的女孩子瞪他一眼,站起来说,“舒原,我是你表姐夫的妹妹。”
谷雨笑起来,“真巧。”
舒原点头,“真没想到,居然真能见到你。”
舒平左右看一眼,拍拍舒原旁边的女孩,指指谷雨的位置,“余欢,你坐过去。”余欢也旁观了这一场相认,笑嘻嘻的拿了碗筷换过去。谷雨也落落大方的站起来,换到舒原身边。倒是舒原有点儿不好意思,横了舒平一眼,说,“哥!”
舒平冲她眨眨眼,跟丁青青继续敬酒去了。
舒原转过身来,对谷雨歉意的一笑,“不好意思啊,我哥这人,有时候神神叨叨的。”
谷雨挥挥手,很不介意的模样,只疑惑的问,“你怎么到南京来了,我记得你以前在北京啊,后来不是还出国了?”
舒原笑,“是在北京,如好姐,”她停一下,解释说,“我的前嫂子,跟我哥在南京上的大学;他们俩恋爱在南京,后来毕业工作就留在南京了,她说死后想葬在这儿,说是守着他们俩恋爱的地方。”舒原有点儿黯然,叹了口气说,“我哥当然什么都顺着她。我去年毕业了,回来工作想陪着我哥,也找到这儿来了。”
谷雨想想,“啊,对,你那时候是说你哥在南京上大学来着。”舒原笑起来,“是啊,他来报道那年我正好高三,学校补课就没送他过来,后来说要来,”她看谷雨一眼,“又赶上南京火车站起火,就又拖下来。”
谷雨微笑,“一晃那么多年啊,真没想到,还能见面。”舒原沉吟不语。谷雨继续问,“新的南京火车站看了吗?非常宽敞明亮哦?要不要去参观参观?”
舒原笑起来,“已经看过了,如你形容的,正对玄武湖,烟波渺渺,十分动人。”
谷雨听这话也不住脸红,嗫嚅说,“那个...是从报纸上抄来的...”
舒原哈哈一笑,注意力转回桌上;谷雨赶紧殷勤的布菜倒茶,舒原也不搭理他,自顾自的吃。
酒席结束已是夜里,众人四散而去,谷雨跟上舒原,说,“我有车,我送你吧。”
舒原斜他一眼,“我也有车。”谷雨愈挫愈勇,拿出名片来写了几个字递过去,“这是我所有的电话,”舒原接过来看看,谷雨再接再厉,“把你的也给我吧。”
舒原终于忍不住笑起来,把自己的名片也掏出来写了几个字给谷雨,笑笑上了车走了。
谷雨心满意足的拿着名片往回走,遇上舒平,舒平看着他笑笑,说,“小伙子,原来你就是谷雨。”谷雨点头哈腰,“是,就是我,就是我,请多指教。”
丁青青在旁边不明所以,却也给他的卑躬屈膝逗得笑起来。
谷雨和舒原,是在网上认识的。那已经是八年前的旧事:舒原大一,谷雨大四。
那阵子大家都泡BBS,全国各地大学的BBS却还没来得及遍地开花,所以天南海北的,都泡在有限的几个地方。
舒原白天忙,总是晚上上线,id就叫夜猫。谷雨那会儿已经在做毕设,是一天到晚都泡线上的人物;他的id注得早,那会儿人老实,乖乖的就把“谷雨”写上去了,好在他这名字看上去半真半假,除了认识的人,也没人知道这是他的真名。
两人第一次碰见倒不是在BBS上,而是个网站的五子棋厅里。那天晚上舒原正好没事儿,就卯住谷雨下了一个晚上。谷雨大二上就编过五子棋的程序,要拿下舒原,简单得就跟吃盘菜似的。
可是舒原偏偏爱下,屡败屡战,屡战屡败:一个晚上下来,战绩惨不忍睹。
不过两人倒是熟得很了。
后来只要舒原上线,谷雨就跟她下棋;舒原跟别人下棋的时候,谷雨就旁观着指点;一来二去的,舒原的水平直线上升。
再后来两人就BBS里聊上了,舒原整晚整晚的跟谷雨泡着,聊天,下棋,见不上就写长长的email汇报每日行程,甚至隔三岔五的打电话问候。但凡有两三日不通音讯,两人都怪想得慌的。
后来谷雨便约舒原来南京玩儿,说带她看看繁华过后的六朝古都。
那阵子正是轻舞飞扬和痞子蔡流行的时分,网恋一下子席卷大江南北。谷雨当时倒真没想那么多,光觉得夜猫这小姑娘挺逗。秋天的南京别有风致,他想这爱下棋的小姑娘一定会喜欢。
若干年后倒回头看,谷雨不得不说自己彼时的邀请颇是居心叵测;然而那个时候,无论是对舒原,还是对自己的同学说起,都是一团正气。
舒原在11月里被他说动,趁着个老师出差的周,买了张去南京的火车票。但她一上车就犹豫开了,千里迢迢的来找一个从没见过面的棋友,这事儿,听起来实在不靠谱。
火车要到站的时候听到广播,说南京火车站着火了,车不能在南京站停靠,转停南京南站,请大家谅解。这个意外的火车站着火,愈发给舒原的犹豫火上浇油。从南京站到南京南站的短短几十分钟,舒原的决心彻底熄灭了,她打了个电话给谷雨,说自己不去了,也没多解释就挂了电话。
两人后来并没有形同陌路,依然偶尔下棋,偶尔聊天,偶尔email;只是,再没有之前的亲密,也不再相互电话;见面的话,也再没有人提起。
后来谷雨毕业读研,舒原毕业出国,又都有了各自的情侣,两人自然而然的疏远了。逢年过节的,偶尔email报报近况,如此而已。
舒原有时候想起那一天火车上主意来回往复的煎熬,恍如隔世。
他们都有对方一张照片,那本是为了在火车站相认用的;八年过后,这两张照片,居然真的派上了用场。
流年似水,物是人非,他们终于见面的时分,居然又都恢复了单身状态。
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
谷雨拿到舒原的电话很受鼓舞,频频约舒原出去吃饭喝茶。舒原也来者不拒,她当年放了谷雨的鸽子,多少有点儿歉疚。
初夏的时候南京的天气终于美丽起来,晴空万里,一城青翠。
谷雨于是约了舒原周末去紫金山踏青。
舒原早早下来,发现谷雨居然骑在辆自行车上看着她。舒原啼笑皆非,“咱们就骑自行车去?”
谷雨也笑,“不,我带你。当年给你安排的节目,迟了八年,还是补上吧。”
舒原无可奈何,只得上去换了身衣服下来。
两人在紫金山走了一整天,数了中山陵的台阶,摸了明孝陵神道上的神龟,又绕着紫霞湖漫步一圈,夕阳西下时分,才筋疲力尽的沿着山道往南京城内慢慢骑回。
谷雨看着前路小心的蹬着车,一边慢慢说,“当时就想带你来这儿的,秋天的紫金山,其实更美。”
舒原笑起来,“现在也不迟啊。”
谷雨接道,“怎么不迟,骨头都老了,走这一趟再加上骑这一趟车估计得回去躺个三四天。”
舒原狠狠拍他一下,优哉游哉在后面唱起歌来。
经过古城墙的时候,正好有人在上面修缮,几个工人纷纷打趣,舒原也不搭理,自顾自的唱,直到南京的满城灯火遥遥在望。
舒原跳下车来,缓步行走;谷雨也跟着下来,推着车在她身边。
悠悠古道,绵绵古城。
舒原叹一口气,两人就这么沉默的走进了城中。
谷雨把舒原送到门口,舒原站住,抬头看他,“今天很愉快,谢谢你。”
谷雨打趣说,“你当然愉快了,我骑车多么辛苦,你只动了动嘴皮。”
舒原笑起来,谷雨注视着她:舒原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眯在一起,鼻子上会有一小团皱皱的纹,象一只小猫。他伸手在舒原鼻梁上摸了一下,舒原顿住。谷雨放开手,轻轻说,“夜猫,你知道的,我喜欢你。”
舒原歪头看他,“现在?以前?”
谷雨凑过去在她嘴角轻轻一吻,“现在是,以前,没见着,不知道。”
舒平听说他们订婚以后说舒原,“你说你瞎折腾,早来南京不就完了,当年还来个临阵脱逃,浪费多少时间,还浪费我的耳朵听你哭诉。”
舒原耸肩,“当年如果来了,也早就掰了:我还在北京读四年,而且还雄心万丈的要出国留学;他有他的路,岔得远着呢。”
谷雨在一旁不置可否,含笑看着舒原,心里却知道她说得对:这些年他们身边的人聚了散,散了聚,聚了又散。时候未到,谁也不甘心安定下来。倘若他们早八九年见了面,彼此早已是记忆中的尘灰,淡无痕迹。
舒原转过来靠在谷雨怀里,满足的一笑,“南京火车站的大火起得正好。”
谷雨拧她,“你看张爱玲看太多了。”
满座哄笑。
缘分,是和对的人,在对的时间相见。
--24节气之春, 完--
楔子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之立春
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
梅红在二十三岁那年的立春上午,生了一个女儿:雪白粉嫩,可爱异常。
下午她婆婆来探访的时候,除了带例行的各种月子食品,还带了薄薄一叠春饼;尽着夸梅红这个时间挑得好:立春生女儿,万象更新,这姑娘势必活泼喜人。
梅红疲惫的倚着床微笑,女儿生下来以后她还没仔细看过,只依稀记得是红彤彤的脸蛋和手脚,肉乎乎的一团。
年轻到底占尽优势,梅红产假还没休完就已经恢复了从前的青春活力。百日抓周的时候,梅红穿着白底大花边的阔摆裙抱着女儿拍照,两张脸都眉目秀丽,比招贴画还要可人。
梅红想,这女儿还是生对了。当时意外怀孕的时候,她如何失措如何紧张,魏林和她如何左右摇摆权衡利弊;如今看来,生下来的决定,到底还是正确的。
梅红坚持要让女儿的小名叫立春。魏林拗不过,只好放得她满屋子“立春立春”的叫唤,只偶尔笑话她说,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屋里呆了个研究种庄稼的痴人,每天介埋故纸堆里研究节气。梅红对此报之一笑。
最后报户口的时候当然还是取了个大名,叫魏琦,写着绮丽,读着端庄。魏林揶揄梅红说,你一定懊悔没生个儿子,不然一定哭着喊着要给他取名叫魏无忌。
梅红没理他,把魏琦这个名字翻来覆去写了几遍,想想又在每个魏琦下面添上立春两个字,心满意足的笑了。
年轻夫妇,情意绵绵,又新添千金,旁人看着都替梅红甜蜜蜜。
立春三岁那年魏林觉得自己在北京的工作发展有限,白日里上班,晚上看书,翌年便申请了个国外的学校去读。走的时候他对梅红母女说,一定会快接她们过去。
梅红本欲阻拦,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让魏林去了:决心一旦下定,不在此时,便在彼时。
魏林一走就是两三年,最终把梅红母女都接出去以后,却跟她说,这两三年他在异乡寂寞无助,跟学校里的一个女同学相互扶持相互爱慕,已是难舍难分。
梅红震惊之下,脱口而出的第一个问题却是:“既然如此,你接我们母女过来做什么?直接回去签字不就好?”
魏林低头,“我觉得对不起你们俩,把你们接出来是我能为你们做的。签字的事儿可以等你找到学校或者别的什么身份以后再做。”
梅红简直啼笑皆非,想甩魏林一耳光却又伸不出手,只得愤愤的在屋里乱转。若是照她少女时代的脾气,这个时候她早就摔门而去;然而日下人生地不熟,女儿又还在屋里睡觉,她要走,也无处可去。
最终梅红还是留了下来,申请了一个跟她从前所学毫不相关的专业学着。
魏林还算长情,一手负责了梅红所有的学费,以及梅红读书期间她们母女的一半生活费。
梅红也不跟他客气,她的积蓄有限,再说,没有了爱,有钱也是好的。
她把魏琦的名字换掉,改叫梅立春。女儿已经半大不小,所幸这三年过的基本都是没有父亲的生活,并不觉得生活里没有了父亲,是多大的缺憾。
梅红飞快的读完了书,带着立春去了明尼阿波利斯工作。
立春在那所城市度过了她剩余的儿童时代,很习惯于冬天绵绵大雪,仿佛永无尽头的寒冷冰封。
梅红告诉她,她的生日,农历上说,是春天的开始:暖风始来,白日也会慢慢变长。
立春因此格外盼望自己的生日,甚至自做主张要把自己的名字改做Spring。梅红帮她到户籍处改了,只是,在家里依然管她叫立春。
立春每年假期到纽约魏林家里过几个礼拜,最初梅红还把她送过去,很快她就发现各大航空公司都有良好的托运小孩的服务,遂放心的把立春交给空姐们。
家庭变故时立春虽小,在后来的岁月里却也慢慢明白了事情始末。最初几年她还会回来跟梅红说有了一个小弟弟,渐渐的她再回到家对纽约之行已经缄默不语。
梅红并没注意,单身妈妈当久了,她的敏感细胞慢慢死亡。
一次立春从纽约回来,进了卧室又着急的扑出来说,“妈妈我拿错别人的行李了。”
梅红与她回屋去查看:果然,行李箱打开里面全是男子的衬衣领带。梅红赶紧合上箱子,却见箱子颜色样式都与立春之前带的显著不同,不禁略有薄怒,指责立春过分粗心。
立春正垂头丧气间,电话响了,是那位拿到立春一箱子少女装的倒霉人。
梅红道歉不迭,那人也不甚介意,只约了个时间地点交换箱子。梅红携立春前去,摁着她道歉。丢失箱子的是位中年男士,文质彬彬,姓方名端,看名字就似个谦谦君子。
他非常幽默有礼,说跟随自己多年的陈旧破烂儿,能跟立春的箱子搞混,十分荣幸。他且补充,为了这个难得可贵的巧合,能否请梅红母女共进晚餐。
那一年立春十二岁,亭亭玉立,人小鬼大,不等梅红犹豫就一口答应。
方端此人性格并不若名字迂腐,言谈有趣,一顿饭宾主尽欢。
梅红才得知原来方端公司总部在纽约,他在明尼阿波利斯和纽约之间,也是常来常往。他听说立春每年至少飞两次纽约,还遗憾的说,可惜没有早点儿被拿错行李。
饭后方端几番坚持要送梅红立春返回,都被梅红驳回,终于还是在饭店门口看着她们母女搭车远去。
立春十四岁的时候,梅红嫁给了方端,并随方端一起迁至纽约。
梅红到了纽约才意识到,她到美国那么多年,从未真正游历过纽约。这个城市,与魏林连接在一起,是她生命中一大伤疤。
立春在纽约的第一个生日,梅红给她买了春饼和烤鸭一起吃。立春吃得满嘴油乎乎的,眉眼都眯在一起。梅红心酸的发觉,立春整张脸,似从魏林的模样复印过来。
春暖花开以后,方端带着梅红逛纽约:鳞次比栉的高楼,呼啸的地铁,水波漾漾的哈德逊河,还有,标志性的自由女神像。
在前往自由女神像岛的轮渡上,梅红看到了魏林一家:魏林的父母,魏林和他后来的妻子,还有两个相差大约三四岁的男孩儿。
躲避已是不及,魏林的母亲先看到了梅红,微微点头示意。魏林见状回过头来也看到了梅红,犹豫一会儿,撇下家人走了过来。
这是数年来梅红和魏林首次见面。
魏林拨开人群向她走过来的时候,梅红突然想起,很多年前,他俩谈恋爱的时候,原是在自由女神像下合影过的。只不过,那是在北京的世界公园,自由女神像在那儿是水池里一个小小的微缩雕像。
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
正感慨间,魏林已经到了面前。方端握住梅红的手,冲魏林微微点头。
梅红神色如常的介绍魏林给方端,方端给魏林。两位男士握手寒暄,交换名片,然后又客气道别。
梅红耸肩,拉着方端要往另一边去。方端却捉住她说,“梅红我有件事儿要坦白。”
梅红抬头,满脸问号。
方端说,“那次立春拿错我的行李,其实,是我们故意安排的。我俩在飞机上飞来飞去碰到过两三次,她主动搭讪我,问我是否有妻室,是否愿意结识她的妈妈。”
梅红大笑,“立春早就告诉我了。不然以立春的糊涂,怎可能记得在行李箱上拴着家里号码的标签。”
方端握住她的手,意在言外的说,“我觉得立春开始我才觉得冬天原来那么长,她叫这个名字再好不过。”
梅红轻轻抱住方端,脸埋在他怀里,“是。我也这么想。”
春天的纽约,天高云淡,哈德逊河映着如洗的天色,泛着一片碧蓝。
人来人往的渡轮上,无数对夫妻情侣,在春天微寒的风中,静静拥抱着,看河中骄傲的自由女神像,慢慢逼近。
梅红与方端,也是其中一对。
之雨水
桃始花,食庚鸣,鹰化为鸠。
前往自由女神像岛的渡轮上,无数对夫妻情侣,静静拥抱。船上气氛温柔和暖,把纽约早春的彻寒,软软融化。
哈德逊河两岸仍有残冰败雪,天空碧蓝如洗。
这是二月末,春寒料峭。
秦欢一个人站在船边,看着河水翻卷上来打着船身,又带着灰白退去,没一会儿,露在外面的耳朵就冻得麻木。
船经过自由女神像岛的时候,停下来放人。
秦欢跟着人流走下来,看看手机,是美国的东部时间下午四点;在北京,应该是凌晨五点。林墨,应该还没醒吧。
她找到背风的地方,拨了长长一串儿数字,电话只响了一声,便听到林墨闷闷的声音问“谁呀?”
秦欢笑,“早啊,墨子。”
林墨叹口气,“哎,欢花儿,猜也知道是你。这年头,没人在这点儿给人电话。什么事儿?”
秦欢嘴上说,“没事儿,就想扰你清梦,”心里却悄悄补充一句,“今天是雨水,墨子。你还记得吗?”
仿佛回答她心里的这句话,林墨在那边说,“今天是雨水了吧?我上个礼拜看了看日历,想着你说不定会打电话来。”
雨水这个节气,对于秦欢,一直别有意义:十四年前的雨水那天,十五岁的她,初见林墨。
那也是个晴天,过完寒假后的第一个礼拜。
班主任从外面带进一个个子高高的男孩,跟大家说,“这是林墨,这个学期开始在我们班学习。”然后就把林墨安插在秦欢的旁边坐。
这是最最老套的一种开始:将近三年的同窗与同桌,两人都是老师的掌心肉;一起被开小灶;一起参加各种竞赛;一起上台领奖;也一齐背地里狠狠咒骂可恶的考试比赛课本作业周而复始。
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平常的起头;他们之间,才永无以后。
其实并不是从没绮丽过:大学以后,两人因为在同一座城市,林墨几乎每天到秦欢宿舍楼下报道。两人还没拉上手,秦欢宿舍的姑娘们都已经自觉自发的管林墨叫秦欢家那位。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吧,两人开始每年庆祝雨水这天。
秦欢说,“这不大不小,也是个节气,是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日子。”林墨就在旁边配合的笑,然后两人就手拉手到小南门外的川菜馆子吃饭:一道京酱肉丝,一道蚂蚁上树,一道鱼香肉丝,还有给林墨的两瓶燕京啤酒。
两人总是吃得满头冒热气的出门;然后晃悠悠走一趟校园;再然后在秦欢宿舍楼下不依不舍的上演一场生离死别戏;最后秦欢伴着楼长每夜例行的“姑娘们,回来了,明天还见呢”的叫唤声,频频回顾着进楼。
这样一晃便是四年。
秦欢原以为和林墨会这样天长地久,相依相偎。
人世间不如意十之八九,可与人说无一二。
争端的开始是因为毕业:对于校园里你侬我侬的鸳鸯,毕业是一场大限:情深绵绵的,干柴烈火的,统统逃不过这一波未卜的未来。
那年的雨水,秦欢记得,是他俩最后一个一起度过的纪念日。
学期开始不久林墨便签了之前谈好一个公司,不料不几日却被告知工作前半年便要外派海外。他来与秦欢商量,能否一毕业就结婚,外派的时候便好申请秦欢一起。
秦欢怎肯愿意,大好青春大好年华,想象中毕业的时候正要大展拳脚。她且说,“何况,你签下这公司的时候,并未与我商量,可见你心中也没有我,谈什么婚,论什么嫁!”
若干年后秦欢回想那夜,总觉得事情本来可以完全不同。然而少年时候怎能知道,彼时真是嘴唯恐不利;心里受挫,愈发要在嘴上讨回来,势必要两人一起鲜血淋淋方能结束。
就这样两人开始冷战。
是时正好秦欢的论文导师谈下来一个海外项目,那边的学校说可以接收一个学生。
秦欢赌气想,“只有你能去海外吗”,遂草草答应导师,迅速补上各种材料,没一个月就收到奖学金录取通知书,然后开始兵荒马乱的护照体检签证。
忙碌的时候时间过得飞快,等林墨终于知道秦欢的去向,已是夏初:一切,已成定局。
秦欢签证成功,被BBS上认识的签友们拉去吃吃喝喝。满座觥筹交错,欢声笑语,她却暗暗心惊:这一条路,再回不了头了吗?
晚上回来,秦欢远远便看到林墨坐在她宿舍楼下的花坛边等。昏黄的路灯把他的影子投在花坛上,折了一折,铺在地上一片暧昧的灰暗。
秦欢心里怦怦直跳,一边佯似镇静的走过去,一边在心里对自己说,“如果他开口留我,如果他让我别走,我一定留下来,再怎么样折腾也不怕。”
然而林墨没有。
林墨也有自己的骄傲:他是来告别的,他来祝秦欢一切顺利学业有成一路平安,然后说希望以后仍然是朋友。
秦欢听到自己微笑说谢谢,然后说很顺利,签证已经拿下来,家里已经在准备行装,还有,“当然,我们当然还是好朋友,墨子”。
那之后林墨再没有到秦欢的宿舍找过她。
秦欢出国之前,高中班同学聚会,两人才又见面。两人神情平静的碰杯,秦欢说“墨子一切顺利”,林墨说“欢花儿你也一切顺利。”
然后又是若干年。
秦欢顺利的拿到学位,签了一个可以四处游历的公司,一路勤勤勉勉的工作,职位稳定缓慢的上升。
她真的和林墨继续做着朋友:不远不近,不亲不疏。
她知道林墨毕业后如约进了那家公司,外派了;回去了;然后升职了;又外派了;又回去了。
并且,秦欢辗转从以前同学哪儿听来,林墨交了论及婚嫁的女朋友,然而不知为何又崩了。
她还知道,林墨的工作,也经常全球天南海北的飞;有些时候,她与林墨两人竟然前脚后脚的到了同一个城市,又前脚后脚的离开。
只是,他们总是相互知道得太迟。总是回到家里以后,打开网络对话,才知道彼此曾经前后几天,走在同一片天空下,甚至,走过同一家商店,看过同一场游行。
是哪里出了错呢,秦欢想,为什么,那么广大的世界,他们被送到同一个地方,却没有遇见。小说里不是常有撼动人心的重逢吗:在陌生的城市,陌生的街角,一举目,一转头,便看进对方的眼睛里,天荒地老。
难道他们的缘分,只得那么多而已。
秦欢二十九岁那年的立春,与同事一起参加公司里老好方端女儿的生日宴会。
那姑娘十五岁,粉红脸颊笑起来有深深酒窝。宴会完毕秦欢留下来帮忙收拾,旁听那姑娘与母亲娇嗔的对话,又是可爱又是可气,一时不觉怔忡:十五岁,那是她与林墨初识的岁数。
一转眼,已经那么多年;一切却还在原点:两人是朋友,也只是朋友。
入夏不久秦欢适逢公差回到从前读书的城市。
那并不是她第一次重返故里,却是第一次重游故地。
她摸索着找到从前跟林墨吃饭的地方。饭馆却是没有了,只有一条宽敞的马路,载着滚滚车流。
盛夏的下午,她孤零零的在路上走来走去,舍不得离开,却也找不到能坐下缅怀的地方。
一切都已太迟,她想。一切,都已经太迟了。
然而命运却不这么想。
秦欢在路上来回走了几趟,失魂落魄的站到路牙边要打的,却有车猛地从中间换了两三条线别到路边,吱一声停下。
秦欢疑惑的低头,看到林墨在驾驶座上,对她微微一笑。
又过了两年,秦欢向公司请调,要求调回从前自己读书的城市,林墨也换了个不再满世界跑的职位。
秦欢和林墨认识后第十七年的雨水,他们结婚了:静悄悄的领了证,然后在一个小小的饭馆里,点了三个菜,两瓶啤酒;再然后,林墨一路开着车到从前秦欢的学校里,远远的停了,两人慢慢走到秦欢过去宿舍前的花坛。
那一带已经在一修再修下变得面目全非,周围却仍然围满了依依不舍道晚安的年轻情侣。
夜幕里没人注意秦欢和林墨这对不合时宜的中年人。
林墨就着黑握着秦欢的手,两人天南海北的闲聊,说从前一起去过却错过的城市与风景。他突然问秦欢,去过的地方,她最喜欢哪里。
秦欢笑笑而过,并不回答,很快岔过这个话题。
两人转了一小圈便自离开。秦欢抬头看路灯,这灯奇异的数年不变,连灯光都一样的昏暗。她看到脚下两人的影子拖得长长的,并在一起。
世界上我最喜欢的地方,是你身边数尺方圆。
之惊蛰
獭祭鱼 鸿雁来 草木萌动
即使是接近午夜时分,大学的校门口依然人来人往,灯火辉煌。
苏涵就在这时稀时密的人流里,与秦欢林墨擦身而过。
是秦欢先看到的苏涵。
苏涵听到秦欢叫他,便停住,然后看到秦欢一身红衣,从树影间向她跑过来。待秦欢跑到面前,苏涵才说,“我收到你的邮件了,怎么,兜兜转转那么多年,还是回到林墨身边了?恭喜你啊!”
秦欢却不答,急急忙忙的问,“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也不说一声?”
苏涵顾左右而言他,“怎么这么巧你们也来这儿故地重游?”
两三句寒暄的功夫,林墨已经走了过来。他冲苏涵点点头,揽住秦欢,“欢花儿,晚了,我们也该回去了,你让苏涵自己走走吧。”
苏涵感激他的细心,秦欢却不依不饶,问出了苏涵在这儿的联系方式方才离开。
苏涵看着他们并肩而去,却是没了再进这校园故地重游的心情。
两情相悦以后回来看旧时旧事,是要看流年变幻而人不变;自己这般,却是物换人非事事休,又有什么趣味。
他点了支烟,站在大门口。
便是这一支烟的时间里,苏涵想到,原来,今天是雨水,难怪秦欢林墨要选此时访此地。
雨水过后,便是惊蛰了。
苏涵原本并不是对节气敏感的人,然而大学里认识了秦欢,受了她的影响,不免对节气也注意起来。
苏涵是林墨的大学同学,因他而认识秦欢,跟秦欢却比跟林墨要亲近很多;归根到底,也是因为十年多前惊蛰那天吧。
秦欢那天原来是跟林墨约好了来找他的,结果因为出门晚了忙中出乱一头扎进苏涵的宿舍,迎面就撞见苏涵用刀在自己的手腕上划拉。
他记得秦欢貌似镇定的给他包扎好以后,揪着他说闲话,“苏涵,你知道吗,今天是惊蛰。节气上来说,今天的雷,是要惊醒蛰伏在地下的冬虫的。”
当时的自己漠不关心的笑了一下。
如今想来,确实讥讽,自己选来向喜欢的人出柜表白的那天,居然如此蕴涵深意。
苏涵踩灭了烟,伸手出来看了看:一晃十数年,当年留下的伤疤已经淡了,只有一片杂乱无章的白痕,自己多年来不离身戴着的手镯留在手腕上的印子,似乎倒还深些。
无论如何,苏涵想,他还是要感谢秦欢那天的匆忙,也感谢自己居然没有锁门。
很多事情,冲破了关口,回头再看,便是一片清明;只是当时,总是一片迷茫。
那之后是苏涵搬到了林墨所在的宿舍,与从前形影不离的朋友突然变成陌路。身边好奇和劝和的人,都一拨接着一拨,甚至一直到毕业散伙饭上,还有人劝酒。
没有人知道真相,苏涵不说,那个人当然更不会说。
直到大家各奔东西,只有秦欢,这个苏涵因缘际会交上的朋友,才知道始末。
真相其实简单,只是没人猜到:苏涵爱上他的朋友;而他的朋友听到表白以后对他避如蛇蝎。
同性恋,即使今天,在社会得到的接受程度尚且有限;何况是十数年前不知所以的大学男生。
后来苏涵飘洋过海,跟从前几乎所有的同学朋友都失散了联系。
一个人在异乡,仿佛是可以从头再来的。只是,走得再远再陌生,总归还是有想回来的一天。
人生长远,不能忘的,似乎总是起点。
那个起点,对苏涵来说,是多年前的惊蛰,惨烈的告白,和更加惨烈的绝望。
第二天苏涵果然接到秦欢电话,上来第一句话居然就是“苏涵你还是一个人?”
苏涵无可奈何,“秦欢,你新婚燕尔怎么不出去蜜月旅行,还在这儿耗着干吗?”
秦欢继续问他,“你是回来发展,还是只是探亲旅游。”
苏涵说是探亲,一两个礼拜以后就回去。
秦欢立即约了见面的时间,她说,“倘若你回来发展,来日方长,我们慢慢再见不迟;既然你马上要走,咱们这就见。”
他们约在雕刻时光,两层楼的新地方,新装潢:透亮的玻璃和宽敞的场地,再也没有从前的挤逼。
一杯咖啡,喝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苏涵也不得不放弃抵抗,答应秦欢的相亲。
秦欢得意洋洋,“我给你物色很久了,机缘巧合,也是最近才辗转从朋友那儿认识这个人,人家也是单身,也跟家里出了柜,我考察过了,无论才华相貌性格在同志里都算拔尖儿。”
苏涵到这会儿要苦笑也笑不出了,只叹口气说,“我对你们家林墨,真是充满敬意。”
秦欢态度强硬,拍拍他说,“我已经跟人家约好明天了,就这儿,下午三点。你没事儿吧?”
苏涵翻个白眼,“大姐,我说有事儿你能让我不来吗?”
秦欢点头,“很好,大姐我明天下午两点给你电话,免得你忘了。”
苏涵第二天如约到了雕刻时光,暗想,祖国大地还真风气开化,连同志相亲都遍地开花了。
这么想着,后来跟方礼桐把杯言欢的时候,心里多少还是有点儿游戏心理。
方礼桐后来说,“咱们第一次见面,你怎么总是个神游太虚的表情,我哪儿入不了你的眼,让你目光游离神情可笑啊?”
那已经是数个月后在苏涵湾区的家里,方礼桐坐在苏涵床上,衣冠不整的翻阅苏涵过去的照片簿。
苏涵看着他,百思不得其解,“你这样的人,怎么会答应秦欢的相亲主意?”
方礼桐嘻皮笑脸,“我回去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秦欢把你吹得天上有地下无,我想见识见识,再不成也可以解决一夜。”
苏涵想也不想就把手里的东西砸出去,方礼桐顺手接住,给了另一个答案,“我看了我今年的星象书,说我红鸾星动,必有奇缘。然后我看到你手上样式古怪的手镯,觉得异人就是你了。”
苏涵懒得理他,方礼桐却在这时刻合上相本,正色说,“我其实是好奇。你知道,那天我跟我堂姐喝茶,因为是在她们公司的茶餐厅,那么巧就赶上秦欢坐在旁边。堂姐要把我掰直,一顿饭不断给我介绍她认识的适龄姑娘,我只好重申自己只爱男人,秦欢就从旁插口了,问了我半天,然后她就说她可以给我安排相亲,跟男人的。我拗不过她,又想摆脱堂姐,就答应了。”
苏涵揉揉额头,不错,这个原因最像真的。
方礼桐却看着他说,“我答应以后以为秦欢过段时间就忘了,不料没几天她就电话我订了时间地点。我去之前也觉得不可能是真的,天下那么大,哪里有那么巧,两个都在湾区呆着的中国同志,都挑了那一小段时间回去探亲,又赶上秦欢这样的人物给牵在一起。我看咱俩就该一块儿,想跑也跑不掉。”
苏涵嘴上一笑,说,“有什么稀罕,一半以上的海外中国同志都在湾区,那里面一半以上的人都挑春节过后回去探亲,避免拜年的麻烦。”
话虽如此说,苏涵也换到了床边,挨着方礼桐坐下,翻开照片簿给他说照片里的掌故。
方礼桐不久退掉自己的房子,搬来与苏涵同住;连苏涵自己都不敢相信,这样一个蹊跷的起点,两人居然安定下去。
第二年苏涵和方礼桐联名给秦欢寄去一张庆祝结婚一周年的贺卡,落款的时候,方礼桐看苏涵落了个xx年雨水,好奇地说“想不到你对节气还有研究。”
苏涵放下笔,对方礼桐一笑,“是啊,雨水下来,是惊蛰。节气上来说,惊蛰那天的雷,是要惊醒蛰伏在地下的冬虫的。”
方礼桐瞪着苏涵,不知所以。
苏涵揉着左手腕上的手镯,戴得久了,这手镯竟如长在自己手上一般。他问方礼桐,“你知道我跟秦欢怎么认识的?”
方礼桐摇头。
苏涵继续说,“她先生林墨,是我大学同学,我大学的头两年,宿舍跟林墨的正好挨着。”
苏涵本来以为会讲很久,不料短短数句,就把前因后果全部交待明白。方礼桐听完很镇定,还拿来苏涵的相本,问他可有此人照片。
苏涵摇头,那仿佛已经是前生的事了。
十数日后便是惊蛰,苏涵回到家,发现方礼桐一个人坐在黑暗里。
他顺手拧开灯,问方礼桐“干吗啊你,一个人在家也不开灯?”
方礼桐走上来,一本正经地说,“苏涵同学,我爱你。”
苏涵平地打个冷颤,推开方礼桐,“神经病。”方礼桐笑起来,凑上来看苏涵的手腕,不等苏涵反应过来就拨了他的手镯,轻轻说,“已经看不见了。”
苏涵沉默的一笑,方礼桐继续说,“从今以后,惊蛰,就是我向你表白而且你欣然接受的日子。我们要每年庆祝,一直到老。”
苏涵这才醒悟过来,神色复杂的看向方礼桐。
后来秦欢致电苏涵,说,“你知道事情有多巧,如果那天我和林墨不是正好在那个点儿从你们学校出来,如果我那天在公司午餐选了另一张桌子,如果方礼桐的堂姐没有逼到他在茶餐厅表明同志身份,你们就见不着了。”秦欢叹口气,“真巧啊,我说你俩是缘分天注定。”
苏涵闷声说,“秦欢你是想说你自己是天吗?”
秦欢在哈哈大笑中挂了电话,正好方礼桐推门而入,说,“啊,原来你也在啊。我们公司安排了周末烧烤,要携带家属,我们一起去吧。”
苏涵微笑。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遇见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原来你也在这里。”
之春分
玄鸟至 雷乃发声 始电
湾区的春末夏初,空气中依然有雨的微潮,阳光却是暖洋洋的灿烂。苏涵跟方礼桐烧烤回来,吃得满嘴流油。
回到家门口,刚下车,看到一女子坐在台上,裹着厚厚的大衣,守着一具硕大的行李。
苏涵看看她,确认自己不认识;然后转头看方礼桐。只见方礼桐一脸牙痛的表情迎上去,嘴里说,“梓分你怎么来了?”
关梓分站起来,温婉平和,微微点头说,“家里出了点儿事儿,必须马上回去;但是我只能买到明天早上从三藩出发的机票,礼春说让我在这里叨扰一夜。”她目光从方礼桐换到苏涵身上,一脸抱歉,“对不起,礼桐哥,我以为礼春已经跟你说了。”
方礼桐还没开口,手机响起来,他掏出来看看,嘴里说,“嗯,他正要说。”,一边说一边接起电话,嘴里嗯嗯啊啊几句,然后说,“梓分在呢,要不要说话?”
关梓分站起来,正要走到方礼桐身边,方礼桐却又嗯了一声,挂了电话,嘴里讪讪的说,“礼春说,他会在南京接你,祝你一路平安。”
关梓分脸色明显黯淡了一下,继又礼貌的说,“打扰了,礼桐哥。”
方礼桐拍拍苏涵,对着关梓分说,“你们还没见过吧,苏涵,我的partner;”关梓分向苏涵微笑示意;方礼桐又指指关梓分,“关梓分,我弟的……”他支支吾吾半天,“那个,好朋友。”
三个人一起进了门,晚上安排好关梓分,苏涵靠着窗点了支烟看新到的杂志,方礼桐在旁看他,“你一点儿也不好奇啊?”
苏涵抬头,“什么啊?”方礼桐凑上去一起看他手里的杂志,“关梓分呗。”
苏涵笑笑,“有什么可好奇的,你弟的准女朋友?”方礼桐有气无力的挥挥手,“不,不是。哎,他俩一笔烂账;啊,不,更正,我弟一笔烂账。”
苏涵似笑非笑,“我看你就能看出来。”
关梓分怕误了飞机,第二天由方礼桐早早送到机场了,一飞十几个小时到了北京,关梓分连机场都没出,走了几圈,又换到飞往南京的登机口。
到了南京,方礼春果然在出口等着,一贯的风流劲儿,旁边不少女孩子走过都偷偷转头看。关梓分远远看到了,一阵疲惫。
正这会儿方礼春看到她了,殷勤的迎上来,接过她手里行李车,体贴的说,“坐飞机累了吧,你别着急,你外公目前情况还稳定。”
关梓分默默点头,由着方礼春把自己手里的东西接过去。
一路上关梓分都沉默着,由着方礼春喋喋不休的说话。最后她终于忍不住,敲敲前窗说,“礼春你安静一会儿吧,我头疼得很。”
方礼春立即住嘴,把关梓分送到她家。关梓分的母亲迎出来,老太太精神还行,看到方礼春还热情的招呼他进来,方礼春还没说话,关梓分已经打断她母亲,说,“妈,不用了,礼春还有别的事儿。”
方礼春见风使舵,赶紧附和,放下东西就走了。
关梓分走进自己的屋子,关上门,一路的疲倦如潮水般卷上来,她终于昏昏沉沉睡过去。
方礼春出来开着车,又接到方礼桐电话,嘴里哼哼哈哈的说,“嗯,接到了,知道了,哥你真罗嗦。”
方家跟关家毗邻而居,他和关梓分更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两人出生那天正好春分,于是一人分一个字:梓分先出生,挑了“分”字,他便轮到“春”。
这么些年两家若有似无的期待,以及梓分掩饰的热情,他都能感到看到。然而方礼春生就风流性子,再加上皮相上的倜傥劲儿,他并没有安定的心思,至少现在没有安定的心思。这些年他从来没有招惹过梓分,却也没有疏远过梓分。方礼桐屡屡教训他,“你若不喜欢人家姑娘,早点儿给人了断,别把人吊着,放也不放,吃也不吃。”他嘴上应着,行为却是依然故我。
二十余年的青梅竹马,方礼春相信梓分愿意等他,等他收心。
关梓分第二天早早就醒了,自告奋勇去火车站接姨妈。
南京火车站正对着阔大的玄武湖,清晨的太阳圆圆的一轮斜斜的挂,空气迷迷蒙蒙的,太阳的颜色也不甚新鲜:一切,都像截自一部陈旧的电影,带着将褪未褪的颜色,疲惫又执著。
结果火车晚点,关梓分一个人在车站等了又等,最后姨妈姨丈跟一个高个男子一起走出来,满面感激。
关梓分迎上去,才知道这一路火车甚多变故,时间交错,车中爆满,姨妈念叨,多亏这男子多有照料,才能平安顺利到达。关梓分谢了又谢,那男子虽然外表零乱容貌粗犷,为人却是谦和有礼,几人互相致意半天,才四散告别。
关梓分的外公没有平静很多天,就撒手西去。因老人聚过来的一家人,悲戚戚的办了丧事,又分头离去。
关梓分假期告罄,自己也收拾着预备回去。她公司年初把她外派到北美,说是半年既返,如今半年过去三个多月,自己又如此折腾一遍,时间也剩余不多。
走的那天是方礼春送她。关母经此不幸,精神甚差,但依然殷殷叮咛;方礼春也异常客气体贴,说是拿了假要把关梓分送到北京,请老人家放心等等。
关梓分与外公并不算亲近,然而生离死别总是大不幸,她一路沉默;方礼春也异常温柔,二十余年里少有的如恋人般的周到呵护。
关梓分上午到了北京机场,下午即要飞走;她无意问起方礼春什么时候返回南京,方礼春支支吾吾,说既然来了北京,顺便看看朋友云云。关梓分见状心中明白,也不再问。
飞回美国的航班依然热热闹闹的一机人,关梓分依然早早托运了在候机厅里等着,自行看书。不料坐了一会儿,有个男子过来招呼。关梓分看他半晌,心中默默回想,才意识到是那日在火车站接亲戚的时候遇到的热心人。
那人自我介绍叫山河,关梓分听他名字有趣,两人便有来有去的聊起来。
话匣一开,却发现两人居然兴趣相投,爱好类似。更巧者,山河便在关梓分所在的地方,也是进修外派,比关梓分更早半年,预定的结束时间却是相近。
两人一路回去,山河又把转机的班次换到与关梓分一致。二十余小时后两人抵达时,关梓分说话已经说得口干舌燥,然而内心却平静欢喜。
两人约了周末打球爬山,然后便一周一周持续下来。
山河关梓分都爱喝茶,也都挚爱普洱。两人周末运动完毕,总是在关梓分家消磨晚上。关梓分细细烧水洗壶,又将温水洗茶,最后做一壶普洱与山河分享。
关梓分用白瓷杯,山河用玻璃杯。上好的普洱,灯光下看犹如红酒,芳香醇厚。
两个月以后,山河的培训结束,关梓分的也是。山河把自己的东西统统收拾好运送回国以后,过来帮关梓分收拾。
关梓分开了门,伊赤脚站在地上,头发胡乱盘着,穿着工装吊带裤,手上戴着厚厚的橡胶手套,一脸疲倦。
山河笑起来,“怎么了,要回家了还一脸苦相。”
关梓分拼命挤出一丝笑来,“满屋子垃圾,扔也扔不得,留也留不得。”
两人在关梓分的屋子里收拾了一天又一夜,关梓分的屋子里的纸箱堆了半墙。末了她从橱柜里又抬出一个小纸盒,默默封胶。
山河笑起来,“还有什么宝贝,值得如此珍重。”话说完眼睛却瞟见盒子上小小的一行“礼春”字样,心中极悔,连忙住嘴。
方礼春此人,山河是知道的:平日里听关梓分说起不少,虽然没什么缠绵悱恻的故事,听起来往往让人默默叹气。
关梓分看山河一眼,把这小盒子放到方才有空的纸箱里,一边招呼山河过来帮忙封箱。山河过去,把箱子密密封好,握住关梓分的手,把她拥进怀里。
两人在那一周的周末离开美国。
方礼春仍然去南京机场接关梓分。关梓分与山河一同出来,看到方礼春微微而笑,把方礼春介绍给山河说“方礼春,我跟你说过的,我们家邻居,我们快三十年的青梅竹马。”
山河温和的笑,伸手与方礼春相握,“山河。”
关梓分在旁边补充一句,“我男朋友。”
第三年春分,关梓分新生的儿子满百天,她与山河把家中所有满满摆了一地,小家伙藕节一样的小手把每件都摸了一遍,最后抱了个小足球心满意足的玩了一天。
太阳落山时分关梓分的母亲把孩子接过去,山河便和关梓分出去吃饭。山河特地开车绕到南京火车站边,嘴里说,“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关梓分抿嘴,“我能不能不记得?你当时衣冠不整头发蓬乱,真正狼狈。”
山河大笑,伸手在关梓分头上胡乱弄。关梓分看看窗外,说,“山河你知道吗,今天是春分。春分乃半,今天是春天的正中间。”
山河眨眼,“我知道,这一天,在北半球昼夜等长,再往后天气渐热,白天渐长,夜晚变短。”
关梓分微微颔首,“是,白天越来越长,而晚上,会越来越短。”
这一天关梓分三十一岁,方礼春也是。
三十一年前,他们两人,一人在清晨出生;另一个,在夜晚。
之清明
苹始生 鸣鸠扶其羽 戴胜降于桑
江南的清明时节总是细雨绵绵,这一天是一年里公墓区人群最是稠密的一天。
关梓分与山河还有家中亲戚拜祭完外公,沿着山道缓缓拾级而下。迎面走上来一个一身黑衣的女子,面容秀丽凄切。经过关梓分的时候她不小心碰了梓分一下,本是最微不足道的一点儿轻撞,她却涕泪齐下的道歉起来。梓分不住地说没关系,担心地问她可好;她只掩面,匆匆忙忙踉踉跄跄的迈上去。
山河拉住了想跟过去的梓分,他说“到这儿来的人,多半都有伤心事。”
关梓分抬头看,满目是密密麻麻雪白的墓碑,一行一行,一列一列。她低头,与山河携手下山。
而那位撞了她的女子,却在这个时候停下了脚步,呆呆的看着梓分与山河并肩而去的背影。
只差那么一点儿,只差那么一点儿,常风,我们也可以是这样人人羡慕的恩爱夫妻。
她想起常风那天出门的时候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说“青青,我下午要开会,晚上会回来很晚。”她还记得自己听了这句话后的赌气,砰的砸上门进屋了。
那天是周日,常风出门以后就再没回来:他在家门口的街口被一辆闯红灯的车迎面撞上,当场毙命。
丁青青之后无数次的想,“我为什么要赌气,为什么不拉着他道别,也许,也许只差那么一秒钟,命运便会完全不同。”
然而人生不能重来,她在生的每一天,都必须为她那一天的赌气,不停懊恼痛悔。
这些年丁青青没有一日忘记常风出门的那一句话,和之后自己狠狠砸门的愤怒;以及,知道常风不在人世以后,她数月的痛彻心肺。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然而,毕竟也是活下来了。
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她的每一天并不比别人的长,她的每一年,一样只有三百六十五个黎明,三百六十五个黑夜。
这已经是她失去常风的第二个清明。
昔日粉红脸颊的少妇,如今只有苍白的脸色。她站在常风的墓前,久久不能离去:这石碑下,长眠着她的爱人,她本以为,可以相守一生的爱人。
舒平远远的站在这一列的墓碑边上看着丁青青。即使隔了十多米,他依然可以看到丁青青的悲戚,这个女子依然年轻,看上去却毫无生气。
他等了整整一个下午,夕阳西下的时候,丁青青终于动了动,离开了常风的墓碑。
舒平在丁青青经过的时候叫住她,他说“小姐,你掉东西了。”
丁青青茫然的回头,舒平说话事出突然,她完全不能理解他说什么。
舒平微微的顿首,索性换了句话,说“你好,我叫舒平,请问你怎么称呼。”
“丁青青。”墓园里的人总是思维缓慢缺乏警惕,丁青青未及细想已经说了自己的名字。
“丁小姐,这个时候天晚了,外出找车一定很困难,让我送你一程吧。”舒平用的是路边登徒子搭讪的话,然而在这肃穆的气氛里,从一身黑衣的他嘴里说出来,却不可疑。
丁青青并不防备,从两年多前起,她已经无所畏惧了。
两人并行下山,舒平小心的让着丁青青,又一路把她载到熟悉的饭馆,自作主张给她点了一碗粥。
丁青青看他,“舒先生,”她的语气很平静,“你不用费力气,我很好,我也没有意思认识新人。”
舒平微笑,并不回答,只示意丁青青喝粥。丁青青并不回绝,她已经过了拿腔作势的时代。
舒平在她对面坐着,看她喝完粥,才淡淡说,“丁青青,我可以叫你名字吧?”丁青青不置可否,舒平接着说,“你不必那么戒备,内人的墓与你先生的挨着,我已经连续两年在那儿碰上你了,你一直没注意过我而已。”
丁青青眉目缓和了一下,却也不说话。舒平继续,“内人去世已经四年了,你的这个过程,我也经历过,总以为自己再也活不下去了,以为自己……”
丁青青打断他的话,“我可以活下去,我已经活下来了。我只是不能再爱。”
舒平微笑,“你可以的,相信我。”
两人不再多说,只共同吃了这一顿饭,然后舒平便送丁青青回去。
丁青青第二天早上看到舒平等在她家楼下的时候,并不吃惊。
后来的日子,舒平有时出现,有时不;两人有时一起吃晚饭,有时不;周末的时候,两人有时一起出去,有时不。
共同的丧偶经历,让两人有心意相同的悲戚和谅解。他们心里都有一道墓;然而他们也都是芸芸众生里普通一员,需要呼吸,需要生活,需要陪伴,需要爱。
时间很快又是一年。
清明的时候丁青青又在墓园见到舒平。她比舒平到得早,特地看了看常风旁边的墓碑,果然有一座是舒平亡妻的,写着“爱妻林如好”,简简单单几行交待了生平,竟是癌症去世。
快中午的时候舒平来了,拿的是一束白百合。
丁青青想起来,这两年每次来都见到旁边的墓有白百合:大朵儿大朵儿的花,芳香洁净。
下山的时候舒平和丁青青一起离开。
那个清明是晴天,两人去了燕子矶。落日染得天边一片灿烂,山石依水,看下去真正半江瑟瑟半江红。
舒平说,“我和小好是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学,大学一毕业就结婚了,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我本来以为我们一定白头偕老。”
丁青青黯然,她原本也这么想。
“我们打算结婚两三年就先要个孩子,就在检查的时候,医生查出小好有宫颈癌,已经是晚期。从知道到她离开,不到一年时间。”舒平叹口气,“我亲眼看着她合上眼,我真不甘心啊。这世间那么多夫妻争吵着要分开,我们明明那么恩爱却不能在一起。”
丁青青伸手过去握住舒平,轻轻说,“情深不寿。”
舒平抹一把脸,“我没什么,其实这些年,慢慢的,我有点儿记不清楚小好的样子了。太久太久没有见面,我有时候回想过去的事儿,老要花很多时间想,她的眼睛是什么模样,鼻子呢,嘴呢,手呢。”
丁青青黯然,她也一样,时间久了,她只记得常风的温和,却渐渐忘了常风的样子。
丁青青说,“你知道吗,从医院出来那天,我站在台阶上看大街。那真是个奇怪的角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一天和平常没什么不同,只是一个普通的周日,车来车往,欢声笑语。而对于我,一切,却都不同了。”
舒平看丁青青一眼,紧紧握住她的手;丁青青回过神来,要挣开却不能,终于还是放手让他握了。
落日迅速的沉了下去,江面方才的波光粼粼也因之消逝;之前的半江鲜红灿烂,竟如一梦。丁青青和舒平并肩站立着,都深深一叹。
活下来的人,需要活下来的生活。再怎样光辉不能忘的过往,再怎么心如刀割的夜晚,时间久了,也就渐渐模糊。
再过一年,两人一同携手去墓园,共同拜祭了常风和林如好,又双双结伴离去。
清明过后,他们登记了。结婚那天丁青青穿一条珠光缎子裙,面颊粉红,微微带笑;舒平握着她的手拍照。拍完以后,两人审视一番,舒平揽过丁青青一吻,说,“真漂亮,非常漂亮。”
丁青青抬头看他,“我们会白头偕老吗?”
舒平心酸,“会的,我在路上一定好好看车,你也一定要按时检查身体。我们都会活很长,很久,很好。”
丁青青怔怔,舒平过去抚她的脸说,“来,笑一笑,今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丁青青拨开他的手,果然一笑,脸颊上浮起一对儿笑涡儿,绚烂如花。
活着,就一定会有新的开始:甜蜜也罢,苦楚也罢;活着,也一定能再爱,再痛,再流泪,再欢喜。
人生总在不停告别,不停出发。
两人并肩走出登记处,外面阳光很好,照得人暖暖和和,是南京晚春少有的大晴天。
之谷雨
桐始生 田鼠化为 虹始见
舒平和丁青青终究还是补了一场酒,请了两边亲密的朋友和家人,也有小小三桌。
那天恰好是谷雨,丁青青跟舒平挨桌敬酒的时候,一个年轻男人站起来,说“表姐新婚快乐!”。丁青青笑起来,拉着舒平说,“这我最亲的表弟,今儿还巧了,他就叫谷雨。”
旁边一个桌子的女孩子听了这话,扭过头来,打量了谷雨一下;谷雨低头看他,两人都颇为惊讶的“啊”了一声,谷雨想了一小会儿,说,“你是......夜猫”。
舒平听到这称呼,忍不住哈哈一笑,坐着的女孩子瞪他一眼,站起来说,“舒原,我是你表姐夫的妹妹。”
谷雨笑起来,“真巧。”
舒原点头,“真没想到,居然真能见到你。”
舒平左右看一眼,拍拍舒原旁边的女孩,指指谷雨的位置,“余欢,你坐过去。”余欢也旁观了这一场相认,笑嘻嘻的拿了碗筷换过去。谷雨也落落大方的站起来,换到舒原身边。倒是舒原有点儿不好意思,横了舒平一眼,说,“哥!”
舒平冲她眨眨眼,跟丁青青继续敬酒去了。
舒原转过身来,对谷雨歉意的一笑,“不好意思啊,我哥这人,有时候神神叨叨的。”
谷雨挥挥手,很不介意的模样,只疑惑的问,“你怎么到南京来了,我记得你以前在北京啊,后来不是还出国了?”
舒原笑,“是在北京,如好姐,”她停一下,解释说,“我的前嫂子,跟我哥在南京上的大学;他们俩恋爱在南京,后来毕业工作就留在南京了,她说死后想葬在这儿,说是守着他们俩恋爱的地方。”舒原有点儿黯然,叹了口气说,“我哥当然什么都顺着她。我去年毕业了,回来工作想陪着我哥,也找到这儿来了。”
谷雨想想,“啊,对,你那时候是说你哥在南京上大学来着。”舒原笑起来,“是啊,他来报道那年我正好高三,学校补课就没送他过来,后来说要来,”她看谷雨一眼,“又赶上南京火车站起火,就又拖下来。”
谷雨微笑,“一晃那么多年啊,真没想到,还能见面。”舒原沉吟不语。谷雨继续问,“新的南京火车站看了吗?非常宽敞明亮哦?要不要去参观参观?”
舒原笑起来,“已经看过了,如你形容的,正对玄武湖,烟波渺渺,十分动人。”
谷雨听这话也不住脸红,嗫嚅说,“那个...是从报纸上抄来的...”
舒原哈哈一笑,注意力转回桌上;谷雨赶紧殷勤的布菜倒茶,舒原也不搭理他,自顾自的吃。
酒席结束已是夜里,众人四散而去,谷雨跟上舒原,说,“我有车,我送你吧。”
舒原斜他一眼,“我也有车。”谷雨愈挫愈勇,拿出名片来写了几个字递过去,“这是我所有的电话,”舒原接过来看看,谷雨再接再厉,“把你的也给我吧。”
舒原终于忍不住笑起来,把自己的名片也掏出来写了几个字给谷雨,笑笑上了车走了。
谷雨心满意足的拿着名片往回走,遇上舒平,舒平看着他笑笑,说,“小伙子,原来你就是谷雨。”谷雨点头哈腰,“是,就是我,就是我,请多指教。”
丁青青在旁边不明所以,却也给他的卑躬屈膝逗得笑起来。
谷雨和舒原,是在网上认识的。那已经是八年前的旧事:舒原大一,谷雨大四。
那阵子大家都泡BBS,全国各地大学的BBS却还没来得及遍地开花,所以天南海北的,都泡在有限的几个地方。
舒原白天忙,总是晚上上线,id就叫夜猫。谷雨那会儿已经在做毕设,是一天到晚都泡线上的人物;他的id注得早,那会儿人老实,乖乖的就把“谷雨”写上去了,好在他这名字看上去半真半假,除了认识的人,也没人知道这是他的真名。
两人第一次碰见倒不是在BBS上,而是个网站的五子棋厅里。那天晚上舒原正好没事儿,就卯住谷雨下了一个晚上。谷雨大二上就编过五子棋的程序,要拿下舒原,简单得就跟吃盘菜似的。
可是舒原偏偏爱下,屡败屡战,屡战屡败:一个晚上下来,战绩惨不忍睹。
不过两人倒是熟得很了。
后来只要舒原上线,谷雨就跟她下棋;舒原跟别人下棋的时候,谷雨就旁观着指点;一来二去的,舒原的水平直线上升。
再后来两人就BBS里聊上了,舒原整晚整晚的跟谷雨泡着,聊天,下棋,见不上就写长长的email汇报每日行程,甚至隔三岔五的打电话问候。但凡有两三日不通音讯,两人都怪想得慌的。
后来谷雨便约舒原来南京玩儿,说带她看看繁华过后的六朝古都。
那阵子正是轻舞飞扬和痞子蔡流行的时分,网恋一下子席卷大江南北。谷雨当时倒真没想那么多,光觉得夜猫这小姑娘挺逗。秋天的南京别有风致,他想这爱下棋的小姑娘一定会喜欢。
若干年后倒回头看,谷雨不得不说自己彼时的邀请颇是居心叵测;然而那个时候,无论是对舒原,还是对自己的同学说起,都是一团正气。
舒原在11月里被他说动,趁着个老师出差的周,买了张去南京的火车票。但她一上车就犹豫开了,千里迢迢的来找一个从没见过面的棋友,这事儿,听起来实在不靠谱。
火车要到站的时候听到广播,说南京火车站着火了,车不能在南京站停靠,转停南京南站,请大家谅解。这个意外的火车站着火,愈发给舒原的犹豫火上浇油。从南京站到南京南站的短短几十分钟,舒原的决心彻底熄灭了,她打了个电话给谷雨,说自己不去了,也没多解释就挂了电话。
两人后来并没有形同陌路,依然偶尔下棋,偶尔聊天,偶尔email;只是,再没有之前的亲密,也不再相互电话;见面的话,也再没有人提起。
后来谷雨毕业读研,舒原毕业出国,又都有了各自的情侣,两人自然而然的疏远了。逢年过节的,偶尔email报报近况,如此而已。
舒原有时候想起那一天火车上主意来回往复的煎熬,恍如隔世。
他们都有对方一张照片,那本是为了在火车站相认用的;八年过后,这两张照片,居然真的派上了用场。
流年似水,物是人非,他们终于见面的时分,居然又都恢复了单身状态。
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
谷雨拿到舒原的电话很受鼓舞,频频约舒原出去吃饭喝茶。舒原也来者不拒,她当年放了谷雨的鸽子,多少有点儿歉疚。
初夏的时候南京的天气终于美丽起来,晴空万里,一城青翠。
谷雨于是约了舒原周末去紫金山踏青。
舒原早早下来,发现谷雨居然骑在辆自行车上看着她。舒原啼笑皆非,“咱们就骑自行车去?”
谷雨也笑,“不,我带你。当年给你安排的节目,迟了八年,还是补上吧。”
舒原无可奈何,只得上去换了身衣服下来。
两人在紫金山走了一整天,数了中山陵的台阶,摸了明孝陵神道上的神龟,又绕着紫霞湖漫步一圈,夕阳西下时分,才筋疲力尽的沿着山道往南京城内慢慢骑回。
谷雨看着前路小心的蹬着车,一边慢慢说,“当时就想带你来这儿的,秋天的紫金山,其实更美。”
舒原笑起来,“现在也不迟啊。”
谷雨接道,“怎么不迟,骨头都老了,走这一趟再加上骑这一趟车估计得回去躺个三四天。”
舒原狠狠拍他一下,优哉游哉在后面唱起歌来。
经过古城墙的时候,正好有人在上面修缮,几个工人纷纷打趣,舒原也不搭理,自顾自的唱,直到南京的满城灯火遥遥在望。
舒原跳下车来,缓步行走;谷雨也跟着下来,推着车在她身边。
悠悠古道,绵绵古城。
舒原叹一口气,两人就这么沉默的走进了城中。
谷雨把舒原送到门口,舒原站住,抬头看他,“今天很愉快,谢谢你。”
谷雨打趣说,“你当然愉快了,我骑车多么辛苦,你只动了动嘴皮。”
舒原笑起来,谷雨注视着她:舒原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眯在一起,鼻子上会有一小团皱皱的纹,象一只小猫。他伸手在舒原鼻梁上摸了一下,舒原顿住。谷雨放开手,轻轻说,“夜猫,你知道的,我喜欢你。”
舒原歪头看他,“现在?以前?”
谷雨凑过去在她嘴角轻轻一吻,“现在是,以前,没见着,不知道。”
舒平听说他们订婚以后说舒原,“你说你瞎折腾,早来南京不就完了,当年还来个临阵脱逃,浪费多少时间,还浪费我的耳朵听你哭诉。”
舒原耸肩,“当年如果来了,也早就掰了:我还在北京读四年,而且还雄心万丈的要出国留学;他有他的路,岔得远着呢。”
谷雨在一旁不置可否,含笑看着舒原,心里却知道她说得对:这些年他们身边的人聚了散,散了聚,聚了又散。时候未到,谁也不甘心安定下来。倘若他们早八九年见了面,彼此早已是记忆中的尘灰,淡无痕迹。
舒原转过来靠在谷雨怀里,满足的一笑,“南京火车站的大火起得正好。”
谷雨拧她,“你看张爱玲看太多了。”
满座哄笑。
缘分,是和对的人,在对的时间相见。
--24节气之春,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