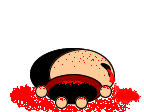好姐妹其人
Posted: 2007-05-21 10:48
好姐妹名皮特而,是个中年人了,年初刚过了44岁生日。他是墨西哥人后裔,长相更近亚洲人,以至认识他以后很长时间都以为他是ABC。当然那也怪我不得,当时我在隔两个门的实验室做电生理,他在这里做电生理。做过的人都知道,电生理这种实验一做起来那是一整天对在实验台子前面,不见天日的;所以我们两个也就是再楼道里碰见,混个脸熟而已。那时的印象就是他一脸严肃,倏忽来去。后来加入实验室,才知道倏忽来去其实是好姐妹的招牌形象。当年跟中西部孩子等人聊天的时候,他形容好姐妹上下班来去飘忽,说:你看有条影子一闪,没了,那就是皮特而。我们实验室应该原来是两间屋,一间大,一间小,后来两间屋中间墙上打了个门,算一个屋,我跟好姐妹都坐在小间,在老板的远端。本来这小间也有个门可以出入,是好姐妹的专用飘忽门。我来了以后椅子在门口,椅子背后放了个氧气罐子,就算封上了。好姐妹只好丛公用门飘忽。他飘忽的一视同仁,恩,应该是老板尤其。他不太爱跟老板说话---当然我也不爱跟老板说话了,但是我比他还话多上一星半点儿---而我刚进来那年,经常老板往我们小屋一探头,问:皮特而呢?我说:走啦。老板一点头,也走了。那会儿我还问过他要是下班走人的话要不要跟人说一声,我的意思是让人家知道你走了,也好锁门五六的。没想到好姐妹反应激烈,眼睛在小长方黑框眼睛背后瞪的老圆,说:我们来去自由,不需要得到任何人的允许!我说:哦,对。心里疑惑他受过什么刺激,闹出来这么大动静儿。后来某次从本系八卦central处得知原来他刚来的时候曾经被老板开除过两次,两次都是他马上拿着实验结果去找老板,老板就又要他了。然后我就某次机会合适的时候找中西部孩子求证及其原因。中西部孩子证实他果然被老板起意解雇过两次,原因是他不听话。我觉得难以想像,因为他自己老觉得自己是个push-over,老板让他干什么都成。当然一个实验室其实很象一个家庭企业,老板让人干什么,很难断然拒绝,所以有一个公平的老板是很重要的。
当然我进实验室那会儿,好姐妹已经温和多了。据给他干活儿的俄罗斯小姑娘反映,好姐妹有脾气。我都不敢相信,追问她说真的假的。俄罗斯小姑娘说,是,他以前脾气挺大的,后来开始唱佛,脾气好多了。好姐妹加入在美国流行的一个挺奇怪的佛教组织若干年,该佛教组织经常集合一批人在家里唱佛。我以前去过他家爬体一次,参加者都是唱佛团的。他还曾经试图转化我跟良人,把我们俩请去他家长谈。我们两个属于坚定的无神论者,坚决没从。转化当天他的男朋友陪坐,俩人样貌相当,更加印证“找男/女朋友是找另外一个自己”这一理论。我估计好姐妹的性格变温和跟他的感情生活稳定也不无关系。好姐妹当年流传出来的一个故事是跟同系一群人喝酒作乐,大家高了以后他把手插进别人的后屁股口袋里去了。现在他则做住家男人状,一说起来丁,他的合作伙伴,怪象个小媳妇儿似的。聊起天儿来,曾经说过丁某晚10点多打算收拾屋子,我说;晚上10点?好姐妹点头说:可不。但是丁要收拾屋子,我只会鼓励他。之后不久,丁的母亲去世,好姐妹说起来的时候还真是叹息怅惘,相当的儿媳妇。还有次跟我抱怨说丁肠胃不合,医生不让他吃油腻食物,结果猜猜他午饭吃的什么?劈叉饼。果然有不舒服了,紧着给医生打电话。我趁机抱怨良人牙口不好,还尽爱吃练牙的东西。
伴随好姐妹生活稳定而来的,乃是一个肚子。这个肚子这两年来日渐显著,让我不由得感慨好姐妹真是中年人身材了。身材虽然中年,但是他待人接物说起话来,还是颇有些teenager的刻薄的。好比有次我们实验室吃饭,他跟中西部孩子搭一个老印度人的车,该印度人开车保守,中西部孩子最后受不了,五条街之外跳下车子步行至饭馆,我们当然都等了好久了,老板问他说怎么回事儿?中西部孩子说:他开车太保守了!然后跟我们形容他如何在交通拥挤的7马路上不肯变线,坚持跟在一特慢的车后面。正说着,好姐妹和老印度人都到了,人见人爱的中西部孩子就不抱怨了,而好姐妹显然是非常的受不了,跟那儿忍不住的要发牢骚,当着开车带他们过来的老印度人。大家都很识趣儿的没接他话儿,他抱怨了两句,看看形势,汕汕的也不说了。这件事情发生在我去没多久,这两年好姐妹说话貌似注意多了,也跟他信的那个奇怪的佛教有关。他曾经给过我一本宣传册子,内容基本上就是正面对人,人也正面对你。当然好姐妹性格如此,不可能一夜变人,时不常还是忍不住要讥诮别人两句,不过这个别人基本不在场。好比最近他手下那个俄罗斯小姑娘大学毕业要申请医学院,我们一致认为她应该申请MD/PhD,好姐妹乃经常把脚架在一圆凳上对她进行说服工作。某日听见一耳朵,他跟俄罗斯小姑娘说起我们老板,说他做薄厚的时候实验做的也就那么一回事儿。这个固然是有趣的信息,但是哈,工作场合似乎还是有点不合时宜。而好姐妹有时侯呢也确乎不会看人脸色。有次研究生院请了个大牛来作报告,院长邀请我们实验室诸人,老板,好姐妹,我和俄罗斯小姑娘去跟该大牛吃午饭。同吃的还有我们系主任。我们系主任是个非常敏锐的人,关于科学的事情,我是不敢没有具体的东西打底就跟他随便泛泛一说的,所以当日午饭,我就往那儿一坐,听大牛跟老板和老板的合作人和系主任说话。系主任明显不爽什么事情,跟那儿抱怨为什么蛋白翻译机制就不能给简化总结成跟能四特公式似的一个公式,我心说那好像不是一回事儿,然后很奇怪为啥系主任对这个那么愤慨。后来跟他的薄厚聊起来才知道原来他们在做的一个控制蛋白翻译的蛋白,做出来的实验结果结果非常诡异。这个是后话,当时我就跟那儿闷声大发财,好姐妹看不过冷场,泛泛一说翻译如何。系主任马上夸夸夸几个问题追加过来,好姐妹乃解释他就是那么一说,系主任看了他一眼,我直替好姐妹后悔。觉得他40多岁一个人,怎么还犯十几二十小孩儿为了说话而说话的错误呢?每每看到好姐妹,就让我这个基本社交白痴对自己的社交能力基本满意乃至自豪。
好姐妹在实验室属于十项全能选手,什么都会做,除了我这个技术工的工。当然我这个技术工也就擅长一个技术,跟好姐妹场纪录,全老鼠行为,全老鼠戳脑子,组织切片染色,荧光染色,西点等等等等,什么都会是没法儿比的。也就因为他什么都会,所以有人做着老板感兴趣的实验没做完半路走人的时候,老板一般就把这个烂尾工程交由好姐妹负责完工。去年我们实验室发出的那篇科学杂志的文章的开始就是这么一个烂尾工程。工程的起始开创人是一个捷克暴瘦小娘,金色短发,蓝色大眼睛,挺东欧美人的美人。她想法很好,也很刻苦,也很爱跟老板说话,就是据好姐妹说手艺不够好。她做了开始的几个实验,结果及时跟老板一汇报,老板大喜,对这个实验结果很兴奋期待。结果捷克小娘因为种种原因在做完试验之前就离开了我们学校,我们老板就让他接手。这个实验是戳活老鼠老子的那种很长的实验,做完一只老鼠需要两天的样子,关键是这两天还不能拍屁股走人;戳完了脑子还得切片染色,都是很繁琐的工作。好姐妹不情不愿的接了活做,经常跟我抱怨说那个捷克小娘手太不利索做出来的东西乱七八糟。不过那会儿我已经习惯好姐妹不说人好,他说啥一耳朵进来先打个7折。结果另外一个做切片的罗嗦老头儿也说她活儿做的粗糙,看来这个小娘活儿做的确乎不够精细。结果就是这个活儿做的不精细的捷克小娘的初始实验,开了本实验室也是我们老板第一篇科学杂志文章的头。这篇文章的实验被好姐妹做完了,发了,结果好姐妹同学在文章排名上跟捷克小娘才并列第一,事实第二。做这一行的都知道,一篇发在好杂志上的好文章之作者排名对于参与者来讲是比梁山泊好汉排座次还要紧的大事。一般来讲,谁排第一就是谁做的实验;排最后的则是实验室大老板。谁排最后一般都没啥争执----大老板么,到这时候都占定了山头了,好比我们这个酶,同行一听就知道是谁的实验室做的。谁排第一倒是经常能打起来----都是打工仔,努力奋斗做老板爬梯子中。不知道好姐妹跟老板抱怨过排名序列的事情没有,要是没有的话,那就是他上次跟人争第一争得都去找学校法律顾问哪里去还没有争到这件事情的经验教训太深刻,灰心不争了。当时听说的时候,我还心里替好姐妹不平了一下儿,接下来却听俄罗斯小姑娘说我们老板写文章书名的时候,还去问过她她都做了什么实验?俄罗斯小姑娘跟我们说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姐妹太不够意思了,人家小姑娘课余时间来替他做那么无聊的试验,而且好姐妹教会了她以后就撒手不管了,人家小姑娘整天对着电脑看老鼠觅食,十几个脑子几百片儿切出来染色,他居然能让我们老板问出来这种问题。我当即就不同情他了。当然这个故事还教育我们,实验做得好不是最值钱的,想出来一个可证明的理论实验比较值钱。
这篇科学杂志文章的发表让我们老板走上了成为大牛的道路。今年他明显就相当的忙,一直应邀在各个地方讲我们这个酶的故事。当然也因为这篇文章,好姐妹找工作的信心和热情大增。想当初实验室那个MD/PhD拿他当慈善事业,背后说起来好像研究生院老人给新人指那个在研究生院做了10年博士的古董级别研究生,教育我---这事儿发生在我进实验室一年左右-----说你看他在这里呆了小10年,只出了一篇像样的第一作者文章,你可不能像他那样儿。好姐妹发了该文章以后,该MD/PhD继续进行其慈善事业,大力鼓舞好姐妹找助理教授位置。这个当然是我们这行儿的下一级台阶,但是要攀上这级台阶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篇好文章。通过我老对各学校招新助理教授的广告之总结,手上没有自己的基金,这个位置就相对难找很多。尤其是名校如康乃尔哥伦比亚,应聘的谁腰里不别上一两篇科学自然神经元细胞类高级杂志的文章,好姐妹手里只捏了一篇并列第一的科学文章,实在算不上竞争力强劲。在这个MD/PhD的鼓舞之下,好姐妹开始了应聘助理教授的漫漫长路。第一轮下来,都被拒掉了,跟本校另外一个系的系主任申请了一下儿,应为该系主任不够爱他,没成。----这个系主任爱我们实验室出身的一个智利科学青年,该科学青年在座薄厚2年没发文章之后,受聘于这个系主任,年薪高达8万。好姐妹听到这个数儿,夸张地说,眼睛都红了-----实在是太刺激了。尤其是好姐妹自问觉得哪儿都没有比智利科学青年差,而智利科学青年毕竟在两年薄厚过程中一篇文章都没有!------其实这个智利科学青年一看就比好姐妹像科学家,他实在是很有想法,且对科学真的热情。这种人每每让我一碰见就自惭形秽,觉得自己实在是不应该做科学这一行。好姐妹对于科学的态度也属于比较懒散的那种,没有自己特别要追求的某一个课题-----当然现在课题都局部化到某一个蛋白质了,好比我老板追求的就是我们那个酶,这个智利科学青年追求的是一种新发现的酶。我们系主任说过,生物学的重要发现都出现在70年代及之前,之后的工作是在主干上添枝加叶。换句话讲就是比较容易的重大发现都已经被发现了,再做什么做出朵花儿来就很难了。出于这个以及美国研究基金越来越难申请到的严酷现实,我老人家正是考虑跳下科学这条船,因为还没有考虑好应该跳到哪条船里,所以还没有具体进行跳的行动。有天我就问好姐妹他想不想跳去工业界,好姐妹摇头说,还是想要开个实验室自己做老板。对他这点坚持不懈,我是很佩服的。
这几年跟他聊起天儿来,慢慢的也把他的家庭出身拼凑起来。原来他有两个姐姐,其中一个是修女,偶尔电话过来找他不在跟实验室的人话别的时候会说:上帝保佑。跟他父母的关系曾经非常紧张,至于若干年没有说话---没有追问是否他出柜前后,现在貌似关系恢复正常,一说度假就是回加州看家人,闹得他的合伙人丁口出怨言。大学在著名的加州大学伯克里分校,研究生时的老板是个大牛,发现虽然出生后神经元数目变化不大,但是神经元之间交流信息的那个结构对环境刺激敏感,曾经到国会作证以提高幼儿教育环境。他跟着这个大牛的时候发表文章啊,写教科书啊,7788加起来有9篇之多,应该算是非常成功的研究生了。且他还是学校游泳队一员,还曾经正儿八经弹古典钢琴开过演奏会。想象那个时候,好姐妹应该是一个多才多艺意气风发前程无量的英俊少年。结果第一个薄厚没做好,第二个薄厚做了十年才有起色,倏忽一晃10几年过去了,现在的好姐妹已经是个有时身体语言好像9岁小孩儿的中年人了。不过现在他的生活总算上了轨道,看他广种薄收勤恳应聘的样子,就知道他总有一天会在某个学校找到一个真正的工作有一个自己的实验室。
the end
当然我进实验室那会儿,好姐妹已经温和多了。据给他干活儿的俄罗斯小姑娘反映,好姐妹有脾气。我都不敢相信,追问她说真的假的。俄罗斯小姑娘说,是,他以前脾气挺大的,后来开始唱佛,脾气好多了。好姐妹加入在美国流行的一个挺奇怪的佛教组织若干年,该佛教组织经常集合一批人在家里唱佛。我以前去过他家爬体一次,参加者都是唱佛团的。他还曾经试图转化我跟良人,把我们俩请去他家长谈。我们两个属于坚定的无神论者,坚决没从。转化当天他的男朋友陪坐,俩人样貌相当,更加印证“找男/女朋友是找另外一个自己”这一理论。我估计好姐妹的性格变温和跟他的感情生活稳定也不无关系。好姐妹当年流传出来的一个故事是跟同系一群人喝酒作乐,大家高了以后他把手插进别人的后屁股口袋里去了。现在他则做住家男人状,一说起来丁,他的合作伙伴,怪象个小媳妇儿似的。聊起天儿来,曾经说过丁某晚10点多打算收拾屋子,我说;晚上10点?好姐妹点头说:可不。但是丁要收拾屋子,我只会鼓励他。之后不久,丁的母亲去世,好姐妹说起来的时候还真是叹息怅惘,相当的儿媳妇。还有次跟我抱怨说丁肠胃不合,医生不让他吃油腻食物,结果猜猜他午饭吃的什么?劈叉饼。果然有不舒服了,紧着给医生打电话。我趁机抱怨良人牙口不好,还尽爱吃练牙的东西。
伴随好姐妹生活稳定而来的,乃是一个肚子。这个肚子这两年来日渐显著,让我不由得感慨好姐妹真是中年人身材了。身材虽然中年,但是他待人接物说起话来,还是颇有些teenager的刻薄的。好比有次我们实验室吃饭,他跟中西部孩子搭一个老印度人的车,该印度人开车保守,中西部孩子最后受不了,五条街之外跳下车子步行至饭馆,我们当然都等了好久了,老板问他说怎么回事儿?中西部孩子说:他开车太保守了!然后跟我们形容他如何在交通拥挤的7马路上不肯变线,坚持跟在一特慢的车后面。正说着,好姐妹和老印度人都到了,人见人爱的中西部孩子就不抱怨了,而好姐妹显然是非常的受不了,跟那儿忍不住的要发牢骚,当着开车带他们过来的老印度人。大家都很识趣儿的没接他话儿,他抱怨了两句,看看形势,汕汕的也不说了。这件事情发生在我去没多久,这两年好姐妹说话貌似注意多了,也跟他信的那个奇怪的佛教有关。他曾经给过我一本宣传册子,内容基本上就是正面对人,人也正面对你。当然好姐妹性格如此,不可能一夜变人,时不常还是忍不住要讥诮别人两句,不过这个别人基本不在场。好比最近他手下那个俄罗斯小姑娘大学毕业要申请医学院,我们一致认为她应该申请MD/PhD,好姐妹乃经常把脚架在一圆凳上对她进行说服工作。某日听见一耳朵,他跟俄罗斯小姑娘说起我们老板,说他做薄厚的时候实验做的也就那么一回事儿。这个固然是有趣的信息,但是哈,工作场合似乎还是有点不合时宜。而好姐妹有时侯呢也确乎不会看人脸色。有次研究生院请了个大牛来作报告,院长邀请我们实验室诸人,老板,好姐妹,我和俄罗斯小姑娘去跟该大牛吃午饭。同吃的还有我们系主任。我们系主任是个非常敏锐的人,关于科学的事情,我是不敢没有具体的东西打底就跟他随便泛泛一说的,所以当日午饭,我就往那儿一坐,听大牛跟老板和老板的合作人和系主任说话。系主任明显不爽什么事情,跟那儿抱怨为什么蛋白翻译机制就不能给简化总结成跟能四特公式似的一个公式,我心说那好像不是一回事儿,然后很奇怪为啥系主任对这个那么愤慨。后来跟他的薄厚聊起来才知道原来他们在做的一个控制蛋白翻译的蛋白,做出来的实验结果结果非常诡异。这个是后话,当时我就跟那儿闷声大发财,好姐妹看不过冷场,泛泛一说翻译如何。系主任马上夸夸夸几个问题追加过来,好姐妹乃解释他就是那么一说,系主任看了他一眼,我直替好姐妹后悔。觉得他40多岁一个人,怎么还犯十几二十小孩儿为了说话而说话的错误呢?每每看到好姐妹,就让我这个基本社交白痴对自己的社交能力基本满意乃至自豪。
好姐妹在实验室属于十项全能选手,什么都会做,除了我这个技术工的工。当然我这个技术工也就擅长一个技术,跟好姐妹场纪录,全老鼠行为,全老鼠戳脑子,组织切片染色,荧光染色,西点等等等等,什么都会是没法儿比的。也就因为他什么都会,所以有人做着老板感兴趣的实验没做完半路走人的时候,老板一般就把这个烂尾工程交由好姐妹负责完工。去年我们实验室发出的那篇科学杂志的文章的开始就是这么一个烂尾工程。工程的起始开创人是一个捷克暴瘦小娘,金色短发,蓝色大眼睛,挺东欧美人的美人。她想法很好,也很刻苦,也很爱跟老板说话,就是据好姐妹说手艺不够好。她做了开始的几个实验,结果及时跟老板一汇报,老板大喜,对这个实验结果很兴奋期待。结果捷克小娘因为种种原因在做完试验之前就离开了我们学校,我们老板就让他接手。这个实验是戳活老鼠老子的那种很长的实验,做完一只老鼠需要两天的样子,关键是这两天还不能拍屁股走人;戳完了脑子还得切片染色,都是很繁琐的工作。好姐妹不情不愿的接了活做,经常跟我抱怨说那个捷克小娘手太不利索做出来的东西乱七八糟。不过那会儿我已经习惯好姐妹不说人好,他说啥一耳朵进来先打个7折。结果另外一个做切片的罗嗦老头儿也说她活儿做的粗糙,看来这个小娘活儿做的确乎不够精细。结果就是这个活儿做的不精细的捷克小娘的初始实验,开了本实验室也是我们老板第一篇科学杂志文章的头。这篇文章的实验被好姐妹做完了,发了,结果好姐妹同学在文章排名上跟捷克小娘才并列第一,事实第二。做这一行的都知道,一篇发在好杂志上的好文章之作者排名对于参与者来讲是比梁山泊好汉排座次还要紧的大事。一般来讲,谁排第一就是谁做的实验;排最后的则是实验室大老板。谁排最后一般都没啥争执----大老板么,到这时候都占定了山头了,好比我们这个酶,同行一听就知道是谁的实验室做的。谁排第一倒是经常能打起来----都是打工仔,努力奋斗做老板爬梯子中。不知道好姐妹跟老板抱怨过排名序列的事情没有,要是没有的话,那就是他上次跟人争第一争得都去找学校法律顾问哪里去还没有争到这件事情的经验教训太深刻,灰心不争了。当时听说的时候,我还心里替好姐妹不平了一下儿,接下来却听俄罗斯小姑娘说我们老板写文章书名的时候,还去问过她她都做了什么实验?俄罗斯小姑娘跟我们说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姐妹太不够意思了,人家小姑娘课余时间来替他做那么无聊的试验,而且好姐妹教会了她以后就撒手不管了,人家小姑娘整天对着电脑看老鼠觅食,十几个脑子几百片儿切出来染色,他居然能让我们老板问出来这种问题。我当即就不同情他了。当然这个故事还教育我们,实验做得好不是最值钱的,想出来一个可证明的理论实验比较值钱。
这篇科学杂志文章的发表让我们老板走上了成为大牛的道路。今年他明显就相当的忙,一直应邀在各个地方讲我们这个酶的故事。当然也因为这篇文章,好姐妹找工作的信心和热情大增。想当初实验室那个MD/PhD拿他当慈善事业,背后说起来好像研究生院老人给新人指那个在研究生院做了10年博士的古董级别研究生,教育我---这事儿发生在我进实验室一年左右-----说你看他在这里呆了小10年,只出了一篇像样的第一作者文章,你可不能像他那样儿。好姐妹发了该文章以后,该MD/PhD继续进行其慈善事业,大力鼓舞好姐妹找助理教授位置。这个当然是我们这行儿的下一级台阶,但是要攀上这级台阶需要的不仅仅是一篇好文章。通过我老对各学校招新助理教授的广告之总结,手上没有自己的基金,这个位置就相对难找很多。尤其是名校如康乃尔哥伦比亚,应聘的谁腰里不别上一两篇科学自然神经元细胞类高级杂志的文章,好姐妹手里只捏了一篇并列第一的科学文章,实在算不上竞争力强劲。在这个MD/PhD的鼓舞之下,好姐妹开始了应聘助理教授的漫漫长路。第一轮下来,都被拒掉了,跟本校另外一个系的系主任申请了一下儿,应为该系主任不够爱他,没成。----这个系主任爱我们实验室出身的一个智利科学青年,该科学青年在座薄厚2年没发文章之后,受聘于这个系主任,年薪高达8万。好姐妹听到这个数儿,夸张地说,眼睛都红了-----实在是太刺激了。尤其是好姐妹自问觉得哪儿都没有比智利科学青年差,而智利科学青年毕竟在两年薄厚过程中一篇文章都没有!------其实这个智利科学青年一看就比好姐妹像科学家,他实在是很有想法,且对科学真的热情。这种人每每让我一碰见就自惭形秽,觉得自己实在是不应该做科学这一行。好姐妹对于科学的态度也属于比较懒散的那种,没有自己特别要追求的某一个课题-----当然现在课题都局部化到某一个蛋白质了,好比我老板追求的就是我们那个酶,这个智利科学青年追求的是一种新发现的酶。我们系主任说过,生物学的重要发现都出现在70年代及之前,之后的工作是在主干上添枝加叶。换句话讲就是比较容易的重大发现都已经被发现了,再做什么做出朵花儿来就很难了。出于这个以及美国研究基金越来越难申请到的严酷现实,我老人家正是考虑跳下科学这条船,因为还没有考虑好应该跳到哪条船里,所以还没有具体进行跳的行动。有天我就问好姐妹他想不想跳去工业界,好姐妹摇头说,还是想要开个实验室自己做老板。对他这点坚持不懈,我是很佩服的。
这几年跟他聊起天儿来,慢慢的也把他的家庭出身拼凑起来。原来他有两个姐姐,其中一个是修女,偶尔电话过来找他不在跟实验室的人话别的时候会说:上帝保佑。跟他父母的关系曾经非常紧张,至于若干年没有说话---没有追问是否他出柜前后,现在貌似关系恢复正常,一说度假就是回加州看家人,闹得他的合伙人丁口出怨言。大学在著名的加州大学伯克里分校,研究生时的老板是个大牛,发现虽然出生后神经元数目变化不大,但是神经元之间交流信息的那个结构对环境刺激敏感,曾经到国会作证以提高幼儿教育环境。他跟着这个大牛的时候发表文章啊,写教科书啊,7788加起来有9篇之多,应该算是非常成功的研究生了。且他还是学校游泳队一员,还曾经正儿八经弹古典钢琴开过演奏会。想象那个时候,好姐妹应该是一个多才多艺意气风发前程无量的英俊少年。结果第一个薄厚没做好,第二个薄厚做了十年才有起色,倏忽一晃10几年过去了,现在的好姐妹已经是个有时身体语言好像9岁小孩儿的中年人了。不过现在他的生活总算上了轨道,看他广种薄收勤恳应聘的样子,就知道他总有一天会在某个学校找到一个真正的工作有一个自己的实验室。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