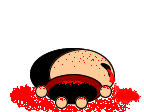最近一篇写大阪河豚料理的,让我想起前几年前11月在关西吃河豚的经历,体验非常相似,记得最喜欢的是刺身,河豚皮和杂炊饭,并且惊叹于带骨河豚的肉感可比猪小排。那间小料理店地方简陋而狭窄,木地板还时常随附近经过的火车而振动,然而食者趋之若骛。
好吃不玩命
from 自・在・空・间
原文:http://tcl.ycool.com/post.3025043.html
我写的游记不会少了吃,日本游,当然,不能少了美食。团餐乏善可陈,好吃的得自己觅。
到日本的第一天,根据事先做的功课,从泉大津坐南海本线到大阪市区的难波,转过一个热闹的市集,到了一条小路上,没走几步,就看见一个大红灯笼,就是他――“太政”。
店面并不大,约六七张桌子,简单的木质桌椅。我们之前只有两个顾客,蛮清净,挺好。
落座,一侧的柜台上面一排店名的小旗,小字是写某年料理大赛的魁首,彰示着不凡的实力。最显眼处,是悬挂着的比篮球还要大一圈的巨大的滚圆的鱼标本,真可称的上王者气象,不是别的鱼,正是我们此行的目标――河豚。
大阪有两大美食出名,一是河豚,二是帝王蟹。而河豚在日本的吃法与中国迥异,中国开禁的河豚是长时间烧熟烧透炖来吃,日本则擅长做河豚刺身和河豚火锅,光看做法就觉得应该是日本的处理法更得本味一些。但日本的这种极限做法是断断不可能进入中国内地的,所以要吃,只有去日本――而且据说日本七成的河豚消费在大阪。按照这个逻辑(或许还得加上我是个嗜吃之人这个理由),我们去大阪,恰好有一餐自理,那么必然是尝试河豚了。
我们所去的“太政”正是大阪料理河豚的老字号,并不同于位在道顿崛美食街上的那些专唬游客的河豚料理店,这家老字号的本店身处幽巷,很有日本当地小料理店的感觉。
菜单是事先功课做好的,两个人,点了河豚菊花刺身两人份,河豚火锅两人份,凉拌河豚鱼皮一人份,火锅河豚鱼皮一人份,河豚鱼鳍泡酒两杯。最后点了杂炊两人份,老板娘连连摇头,比画那意思,你们要一份足够了。――这些也是河豚料理比较标准的配置,只是已不是冬季,否则可以加上精彩的河豚雄鱼的白子。
上来的蘸料有两碟,都是橙醋加酱油的底味,大盅的浓重,是蘸火锅用的,小碟清淡,蘸鱼生的。
那菊花刺身上来真不是一般的漂亮。河豚鱼身上最厚的肉头片成的片,玉洁莹透,展现出一种新鲜的生机,铺展在玻璃碗上,更是让人觉得其高雅精致。顶上点缀的,是一捆细葱段,一块青橙,一片汆熟的河豚片,一撮汆熟切细的河豚皮,一团姜椒辣酱。红绿黄黑白粉,色彩搭配极丰富。

好看不假,关键是吃。老板娘上来说可以拿一片河豚刺身卷一条细葱,蘸小碟调料来吃。我则是出于对第一次吃的食物的好奇,空口先尝了一片。
好吃!河豚刺身,首先质感上就不同于以肥美脆滑为特色的金枪鱼三文鱼刺身,河豚肉质稍韧一些,有嚼头。但片的那样莹薄,吹弹得破,一进口就几乎粘付在口腔里,嚼起,那滋味就更充分的在口舌间洋溢开。鲜!一种特有的鲜味,不加任何作料生吃才能感觉到的纯粹的鲜。我不知道改怎么形容这种鲜,但是正是这种鲜,使我对为什么有人会拼死去吃这种鱼,有了第一层印象,哦,原来如此!
享受过本味的,再蘸小碟的料吃,就觉出这料的好来。好在“本份”。酸是酸,但是这种橙醋并没有一般酿造食醋的酿造味酱香味,只是有橙果的自然清香,只是很自然的给刺身添加了咸、酸,以及来自自然的香。这种味道,一点发酵陈腐气都不带,最能衬托河豚的新鲜活味,所谓“和谐”,只要蘸一点点,就刚刚好。
再来就是卷小香葱的,这葱和上海的小香葱差不多,但是滋味似乎更平和,比小香葱更甘甜,更少辛冲。这令我想起北京前门全聚德那不凡的羊角葱。河豚卷包起这小葱,吃起来更觉丰富,而这葱和调料一样的“本份”,只是更多的衬托河豚的鲜,并不抢戏。
按说随着时间的推移,片出来的河豚肉的新鲜度会有下降。但正是这些调料的得当的调配,使得我们的味觉感官在始终保持精密运转的同时,助力衬托河豚的鲜活,着实难得。
品尝刺身过半,其他菜点也陆续上来,包括河豚鳍泡酒。温热的清酒里浮着两片烤的焦黄的河豚鱼鳍,酒香里夹着一丝焦香。老板娘当着我们的面划着火柴,在酒杯上一掠,淡淡的火焰腾起,持续了几秒钟。老板娘细心的给酒杯盖上盖子,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确认火焰熄灭,就开盖请我们品饮了。
点火蒸腾过的酒,酒精含量有所降低,口味甘冽不冲,淡淡的有烧烤的焦香,酒体也因浸了烤鳍而变成淡金色。这种平和但不平淡的特殊酒品确是品尝河豚的不二伴侣。

一并上来的,还有鱼皮。凉拌鱼皮也是放在一个玻璃碗里,细葱丝,橙醋,调味配料和刺身的完全一样,“无缝衔接”。而汆熟切成细丝的河豚皮,是另一种质感。得力于汆河豚皮火候的精妙,这凉拌,脆,弹,韧,糯,劲,爽,几种似乎互相矛盾互相排斥的口感居然在河豚皮上集中体现,也就是和唇齿有抵抗,但是并不是完全抵抗,嚼咬之间,感觉这胶原蛋白的丰厚,是很独特的。
遍寻我们常吃到的“胶原蛋白”,肉皮,蹄筋,裙边,海参,鱼肚,似乎都找不出一种和河豚皮的质感相近似的食材。而吃河豚皮,一定记得要吃凉拌和汆火锅两种吃法,各有其妙处。而在整个席面上,凉拌河豚皮似乎是一个短小精悍的过场角色,重心自然的过渡到了火锅上――那一堆壮硕肥厚的河豚大块实在太诱人。

火锅河豚肉都是大块的,稍薄一点的是鱼肚子带肋骨的部位,圆浑厚壮的则是带脊骨的。薄的只要煮三、四分钟就可以吃了,厚的也就煮个五分钟,白水煮的,十足本味。待咬到这鱼肉,我忽然明白了,老祖宗为什么给这鱼起“河豚”这名字,肉头的质感和大多数鱼都不同,不松不酥,却是富有弹性和咬劲,里面还有丰沛的膏汁,象极了上好部位的猪肉,怪不得!这肉里的特有的膏汁,是猪肉也无法比拟的,也不象鳗鱼的那种肥,而是带着强烈胶黏感的膏。尤其是贴着脊骨的部分,骨质接近软骨,胶质感更强烈,口味非常棒。这么大块的鱼肉,吃起来极过瘾……到这份上,又不得不说这橙醋调料的好处,爽口解腻,让我们吃个不停。
此时,接着下的是河豚皮,没想到河豚皮还有几种质感。最易烫软的是灰色半透明的部分,不一会儿便成了东北粉条的样子,但是极绵韧,丝毫不用担心会断裂,口味柔滑肥嫩,质感介于鱼肚和蹄膀皮之间。而白色的皮就比较厚,烧一段时间仍保持着一股Q劲,质感近似牛筋海参。黑色的鱼皮也就是背脊上的鱼皮,最厚,醇鲜如裙边,肥韧似鹅掌,滋味不是一般的好。
啖肉吮皮之后,生材盘子里还剩下的就是鱼脸,河豚的头盖到下颚,剜去巨毒的眼睛,以鱼唇为中心,极肥厚的一块。烫煮到鱼头里的胶质成半透明,小心的舀出来,抖梭梭颤巍巍,极诱人。小心的用筷子把鱼牙和鱼骨挑出来,余下囫囵一块,带着膏皮带着活肉,那个美啊。鲜滑柔糯,滋味充盈,口腔里立时洋溢出一种无比幸福的满足感――可与之媲美的,恐怕也只有农历十月里雄蟹的蟹膏了。
吃过这些,再看那锅汤,竟已起稠变浓――都是这些骨肉膏皮所致,轻啜一口,黏黏的象胶水,仿佛要把唇齿粘封起来一样。略下些白菜豆腐煮了煮,吃吃清清口,日本的手磨豆腐很有滋味,白菜也是清甜甘美。老板娘见我们这些吃的差不多了,于是拿来一个木盘,里面有一碗米饭,两个生鸡蛋,一瓶酱油,一碟海苔丝,给我们做杂炊来了。

老板娘一边把葱花和鸡蛋搅打起来,一边盯着锅里的汤,不时撇去浮沫。汤滚起,下米饭,按散,烧煮,再去沫。待米饭完全烧成泡饭粥的样子,沿边浇下葱花鸡蛋液,一手控火,一手推勺,鸡蛋在粥里凝成了漂亮的小黄花。最后淋入一点酱油,那酱油颜色很淡,下去只为调味,并不抢色,一锅杂炊就是米白蛋黄葱绿的悦目颜色,很漂亮。
一人一碗盛来,吃起来,就是两个字,“落胃”!从食物组合上说,这也是原汤化原食,饕餮大餐中不可或缺的一份,作用就象吃烤鸭之后的那碗鸭架子浓汤。不得不佩服这席料理的搭配和程序,启承转合无不严密精妙,河豚这么个吃法,那真是到家了。当然这个只是我事后的理性分析,而我更愿意从感性角度回味这个过程:从计划,期待,到终于实现,这晚的河豚美馔叫我们一次次的触摸味觉颠峰,越吃越兴奋,而这最后的一碗杂炊粥,却是把浓缩了河豚滋味精华的醇汤用极其朴实的方式再次呈现出来,宁静平和,叫人能很容易的平复下来,以一种安逸的心境去享受这一碗粥。而就在这时,你心中最柔弱的部分在不知不觉中被抚慰着了,那种对安全对温暖的诉求得到了某种响应――美食于人,我不想用“征服”,而是想用――“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