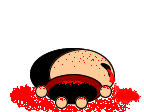盛世2013
Posted: 2010-02-12 4:09
昨天读了陈冠中的盛世2013,很震撼。
我读的时候一直以为陈冠中是画家--后来想起来把他和吴冠中搞混了--看着看着觉得不对劲,反应过来好象看过一篇梁文道采访他的文章。
梁文道采访陈冠中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09/12/ ... _5479.html
从 前我一直都说不準陈冠中的形象。最早他是全华文世界第一个写专书介绍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冷门作者,后来创办《号外》引领城市文化风潮,再后来他写电影 剧本、管理唱片公司……你实在不知道该用哪一套习见的角色去定位这个人。就像我的旧上司梁浓刚,一方面研究拉康,另一方面在电视台任职高层。也许那一代香 港文化人就是这样,见多识广,游歷丰富,但却不太张扬,无论干了多少也许很值得称道的功业,最后都总是好像甚麼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 自从陈冠中定居北京之后,我们对他的印象反而清晰了。原来他始终是个作家,一个锐利的作家。几年前,他开始有系统地书写香港,其自省之深足令不少他的同代 人汗顏,开啟了香港集体反思的精神运动。现在,他以城市观察者的身分,终於交出第一部谈论中国大陆的小说。无论你喜不喜欢,赞同或不赞同《盛世》里的未来 愿景,你都不能否认它的确看得人冷汗直流。谁也猜不到这麼多年之后,竟是一个香港人率先写出中国版的《美丽新世界》。
我在北京和陈冠中聊他的新书,但不免还是要从香港说起,譬如说香港文化感性中那股独特的「冷」。
梁︰ 梁文道
陈︰ 陈冠中
梁︰ 不知道為甚麼香港的sensibility会这麼cool?
陈︰ Cool的确是最贴切的字,香港不喜欢sentimental,不喜欢滥情。
梁︰ 譬如说进念那种剧场,台湾不会有,大陆也不会有。香港很多artist,做installation和行為艺术做了这麼多年,但是从来没有好像大陆这样一做就沸沸扬扬,就让人觉得厉害,觉得是世界第一。这到底是為甚麼呢?
陈︰ 而且就算是很重的一个题材,也要做得轻一点,也要将那个主题说得小一点。我觉那真是某个阶段的西方品味,譬如说五、六十年代欧洲那种存在主义的 品味,或者是后来结构主义与美国的counter culture品味,是cool的,是冷调一些的,就是不喜欢说一些激情大主题,不喜欢激情到连自己也感动。起码我自己就是,整天都想用最简约的方式去说 很多事情。
梁︰ 昨天在我一本书的朗读会中,一位读者就选了一篇我写的东西来读。但我自己其实不太喜欢那篇东西,因為当时我的写作策略是在西藏问题闹得最激烈的时候,特地用很温情的东西去说服一些愤青。我非常不喜欢这种方式,因為它根本不像我,可是有些读者却很喜欢,很奇怪。
陈︰ 大陆的官方论述也永远是华丽的,带感情的,句子和用字都很讲究,就算是中央台的晚会,那些主持人出来说的话都是漂亮的。其实那都是套句,陈腔滥调。这可能是一个训练。即便台湾,比起香港也多了很多感情,香港是特意将感情元素削减了。
梁︰ 台湾很强调一种很温暖、很sweet的东西。譬如他们的唱片,那些印有歌词的小书根本是放不进去CD盒,因為它太厚了,每一页都要有歌者在上面用手写下自己在录这首歌时的心情如何如何,我们香港人看了就会说,有没有搞错。
陈︰ 香港的作家多半也比较cool,由刘以鬯到西西皆如是。就算西西有点童真,有点朴素;或者后来的黄碧云比较「激」,但就是没有那种温情。
梁︰ 所以在这两者之间,香港才有了一个特别的文化的感性存在。这种感性很世故,乃至於我们的电影没有很多温情戏,寧愿喜欢「笑爆咀」,苦中即时求乐。
陈︰ 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已很害怕,不是怕,而是已经开始会去嘲讽「文艺腔」,去拒绝这种东西。起码我自己成长、写作的时候,就很害怕给人说是「文艺腔」。於是这 个「文艺腔」的传统就在香港被切断了。我们又怕被人认為是「扮嘢」,寧愿「存真」也不要「扮嘢」,总之就是不想世界太浪漫,我们对浪漫本身就有疑问,香港 人并不浪漫。我们更不喜欢那些自怨自艾,然后觉得自己很悲惨的情感,譬如说台湾的「悲情」和大陆的「百年国耻」。
梁 ︰ 所以当台湾一份刊物叫我写四九年的香港时,我才发现香港相当有趣,很多人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很惨很失败,我们在香港住了这麼久,你何时听过香港人会这样说? 所以龙应台那本书,就只有台湾人才写得出来。你父母那一代从上海逃来香港,他们会不会常常这样喊苦?没有呀。我认识很多人都是由大陆下来,而且当年还真 苦。但问题就是他们从来不讲,也从来不会拿这些事来说,更不会将这件事变作一种cultural element。
陈︰我父母那一代都好像没有太强调那种苦。他们不会当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整天围绕受害者这个主题,然后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生怎麼会这样苦。我们很快就可以转 换心境。我记得小时候他们有讲过香港是一个福地,说香港真的很好。他们都有一个比较的想法,起码与在大陆的朋友和亲戚的遭遇不同,他们都向前看,很乐观, 然后急急要「搵食」。
梁︰ 台湾是外省人觉得自己很惨,流离失所;本省人也觉得自己很惨,受人压迫。香港人就很少觉得自己惨,反而会觉得自己很幸运。话说回来,你是不是到了北京之后,才更加醒觉香港特别的地方?所以《我这一代香港人》和《什麼都没有发生》都是你到了北京之后才动笔的,对吗?
陈︰ 是,这都是到了北京之后才动笔的。但我觉得那个源头是在七十年代尾,忽然之间自己有一个香港的意识出来了,譬如突然之间怀旧,那究竟要怀念甚麼呢?七十年 代尾怀旧,是想起六十年代自己十多岁时成长的过程。其实那不是很多年后,就在怀念自己十多岁的日子。另外就是觉得香港是我们的家,所以要说说香港。那一种 衝动是最重要的。
梁︰ 那就是办《号外》的时候?
陈: 对,办《号外》的时候。譬如说当年看Q仔(黎则奋)写湾仔,我也觉得很震惊,他把湾仔说得这样有趣。我就觉得,对啊,我们自己的地方也很有趣,那个震惊是 很大的。但是,虽然有了这个意识,却没有去整理它。真的事后回头再看,就是来到了北京才去整理。我92年开始进来,才有一个大的比较去感到大陆与香港的反 差,然后在97年前后开始写《什麼都没有发生》那本小说,连名字都是有比较之下才知道,原来自己长大的地方可能是⋯⋯用文学的语言来说,就叫做「什麼都没 有发生」。
梁: 那是很cool的。
陈: 很cool,相比起台湾和大陆的同龄人来计,如果没有比较就不会想到这一点。这种东西现在想起很幸运,也很平淡。相对来说,我们的经歷是比较平淡。譬如说在大陆,我是属於老三届的。
梁: 你办《号外》的时候有一个很清晰的城市文化意识,对吗?
陈︰我自己觉得《号外》有两个源头,首先是因為去了波士顿,看到当时美国的那个counter culture的「水尾」,就是越战差不多完结,嬉皮士开始淡出,气氛开始静下来的时候。我记得75年我离开波士顿前,刚刚开了一些很新的Disco,一 个享乐年代回来了。我心想,哗,為甚麼会这样?我们前一阵子还在说要对抗越战,还要与政府抗衡,怎麼现在忽然在跳舞?Counter culture是不跳舞的,起码不跟音乐跳,除非你是拉丁人或者是非洲裔,我们当时眼中就只有白人是没有Disco culture的。74年哈佛才有一个大型庆祝会庆祝越战结束,跟着忽然之间就开party跳Disco了。那时候有一些地下报纸,特别是波士顿有The Real Paper,The Phoenix,纽约则有Village Voice。甚麼趣味的都有,很适合我们自己的趣味,从左翼政治到饮食和青年人的生活,包罗万有,然后有很多年青一代才懂得欣赏的幽默,有自己的漫画。我 觉得这种事情我们应该做。
但香港其实是做过的,六十年代的《中学生周报》、《年青人周报》,七十年代的《七○双周刊》,其实都是这类型的东西。然后在七十年代中,忽然之间这种以整 代人作為对象的刊物全部「死掉」,《七○双周刊》已结束,《中学生周报》也结束了,《年青人周报》是硕果仅存,可能还有一两份在喘着气,但最后在76年办 《号外》之前就都没有了。
但我觉得我懂得做,能够编一本这样的东西,能做到美国的那种感觉。所以起初是很模仿西方的,因為那时候比较崇拜英美。当年他们那些小报都叫做「tabloid」,所以我们就叫做《号外》,一开始做了五期双週报,就像是地下报一样。但因為发行太困难,所以才改做杂誌。
梁︰ 当时你们是否都很有意识要说香港的事情?
陈︰ 这反而是迟一些才出现的。我们起初是讲英美,以大学和大学毕业生等年青人喜欢的题材為主。我们对输入新潮洋文化最有兴趣,就是在别人未说起之前,我们先 说,然后才说回自己的成长过程。我们说香港不是由开埠说起,而是从五、六十年代说起;邓小宇的记忆可能去到五十年代,我的记忆可能去到六十年代中段的《中 学生周报》。再加上我们知道成长阶段比我们稍為大一点的人,例如唐书璇这一类。
这两种东西吸引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很多是刚由外面回来的人。我们那一代出道了,读完书回来了,很多在外国学过一些奇奇怪怪的事物,发觉我们的杂誌会介绍 这些小眾的东西,所以他们会聚过来一起做。譬如有次我们写到一些关於同性恋的东西,可能我们的态度写得比较好,立即有人来和我们接洽,表示想替我们写文章 和替我们做点事情,后来就开了一个专栏,叫「少数权利」,其中一个activist叫小明雄。还有一个做时装的朋友刚从加拿大读完书回来,说自己想替我们 编一些时装的内容。当时走过来的全部是同代人,大家集合起来,只不过因為当时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
梁︰ 你们一整代的Baby Boomer留学回来了。
陈︰ 那是第一代的Baby Boomer回来,刚刚开始佔有了一点位置。我们最早的广告都是有一些boomer加入了一些公司,拿到一定位置,然后可以给我们一些广告。在八十年代 初,如果掌权的是个30岁左右,在外国读design回来的,他就会将那些广告先给我们,又或者找我们的杂誌去写一点东西。另外当时有一群人,到底是理工 还是大一设计学院出来的,我都已经忘记了,反正都是学美术的,他们成立了一个「插图社」,对设计很发烧。他们自动跑来找我们说︰「不如让我们替你做封 面。」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力量,而且全部都没有收钱。
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為我们当时没有鲜明旗帜,现在我才想到这事情。如果像是《七○双周刊》这样有一个鲜明的意识形态,也可以聚到一群人,但会是另外的一群。反正《号外》的旗帜不鲜明,就连创刊号都没有发宣言就开始了。
梁︰ 為甚麼会这样?為甚麼会没有创刊词?
陈︰ 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但我连杂誌也不肯储存,我觉得过了就算,没有甚麼大事要说,我们喜欢做甚麼就做甚麼。
梁︰ 这真的「很香港」了。
陈︰ 没错,我们连宣言也不肯写。因為当时我在美国学新闻,有一个新闻记者的态度,但我不肯讲一些很大的态度,譬如先讲一下甚麼关怀呀,完全没有,反而整天都当「知识分子」四个字是搞笑的,更不肯叫自己做知识分子,把它当成是取笑老一辈的字眼。
梁︰ 你现在这种对於《号外》的描述,是不是在你来到了北京之后,回想起才更加清晰?
陈︰ 是,现在就更加清晰一些,但是当初也的确知道,总之见到有趣的,就会把它放进去,见到新的东西也要放进去,时髦的更要放进去。我所谓的「时髦」是我自己心 目中想做的事情。就好像发现一个人很有型,他叫荣念曾,為何他穿的衣服这样阔?那时候大家很流行穿窄衣,他就去穿阔衣,还穿一身黑色的阔衣,这样很有型 呀,原来他从纽约回来,我就决定一定要拉他过来,无论他做甚麼也要给他大篇幅。其实真是没道理,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所做的范畴!就是这样,我们没有甚麼胸怀 大志,要做些甚麼大东西出来的宏愿。
梁︰ 所以后来大家都说《号外》是华文世界第一个城市文化杂誌,其实你们当时根本没有去想这回事。
陈︰ 没有。用「城市」这个字,只是觉得它很有趣。我们最初由Village Voice的原型开始,也参考了《中学生周报》、《七○双周刊》,但它们在消费文化那一面都是比较弱的。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中,美国又有一些新杂誌出来了, 例如讲glamour的有Andy Warhol的Interview,於是我们就学了一些Interview的做法。后来又有份叫New York的真正city magazine,全都是说纽约的有趣东西,我们一套上去,又发现香港也可以这样做,於是我们的副题就叫做「城市杂誌」。
虽然如此,但这个概念当时在商业上是不成立的,整件事没可能成功,但是一直说要结束也没有结束,起码有五次决定要结束,但每次有人肯「夹钱」,又有人肯投 资。好像林秀峰,后来是最大的投资者,但我们不认识他,是他主动打电话来说想投资在我们身上。然后这样子又再捱下去,捱到广告名人施养德进来,说要将杂誌 变得更大,更改版面,使设计变得愈来愈重要。其实之前我根本不知道甚麼叫设计,因為Illustration Workshop,因為施养德,我才知道这是设计。
儘管如此,但那时杂誌的生意还是不行的,直至美国新闻界创作了Yuppy这个字。因為有了Yuppy这个字,於是就有Yuppy產品;当Yuppy產品来 到香港,香港的广告公司便问香港的Yuppy媒体在哪里?而那时全部广告公司都不知道甚麼叫Yuppy,只知道有一份很奇怪的杂誌叫《号外》,那麼乾脆把 《号外》当作Yuppy吧。自此之后就有很多广告了。回看起来是有一点幸运,不然就捱不了那麼久了。
梁︰ 你也挺幸运的,在每一个地方也赶上有趣的时刻。在波士顿时,是某种文化运动的尾声;然后在台北呢,你度过了最有活力的时候,就是戒严前后。
陈︰ 做电影是戒严前,做《号外》就是戒严后。
梁︰ 后来你去台北住,正好碰上了台湾文化出版界和文化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对吧?
陈︰ 是很鼎盛。94至00年我长住台北做有线电视,恰巧是李登辉当上了总统,但未经正式民选,民进党跟国民党吵得最厉害的时候。
台湾发展得很快,94年杂誌已做得很好,书也很蓬勃,甚麼都已经有人做了;有人研究最激进的性解放,很多人写同志,地下的有《破周刊》,有高有低甚麼也 有。台湾在九十年代后的文化是十分完整的,引进外国的东西要比香港做得好,各种各样新的思潮也有人谈论,文化界的地位也比香港高,所以在94至00年间我 写得很少,因為在台湾甚麼也有人写。旧日我能够写东西,许多时是因為没甚麼人写,我觉得我不写,便没人写了。虽然我不是专家,也略知一二。
但我反而在台北写了一本书,是电视剧本,叫做《总统的故事》,后来皇冠把它当作影视小说出版。原本我们打算拍李登辉的故事,请了张大春写十集,平路写十 集,希望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去写,因我知道他俩的态度有点不同。结果二人都写不出来,张大春没时间写剧本,写了个《撒谎的信徒》,但那没可能拍得出来, 因為它不只是谈李登辉;平路一样也写不出来。原来在94至95年,写李登辉是很难的,那怎办?要拍了,於是我自己写了十集出来,由赖建国当导演拍成电视 剧,但后来决定不播了。就因為这样,我下了不少工夫,反而有助於我理解台湾。要从日治时期开始探讨台湾人為甚麼会视李登辉為台湾之子。也许太近了,所以张 大春和平路写不出来。我作為外人反而比较好。
梁︰ 然后你又到了北京。
陈︰ 2000年,别人的时代已超越了我们的。我到大陆,是想做一点网站的东西,怎料人家网股也爆了,阿里巴巴和QQ又已经开了,我还能做甚麼呢?另一方面,《时尚杂誌》集团也在,同时还看着七九八一直旺。后来我乾脆甚麼都不做,写东西算了。
梁︰ 所以香港人在2000年才来北京发展,想打一个庞大的事业是没可能的。
陈︰ 现在的门槛更是太高。我们没甚麼优势,没甚麼比人叻。旧时叻,是因為整个社会走得前一点,你只要跟着自己社会的步伐,便会比人走得快一点点。内地在92年 时和我们有很明显的差距,我记得当时做唱片,根本不宣传,只要找记者写点东西,便卖到不得了,就是这样容易。
梁︰ 你在《号外》时期写的东西跟现在的不同,现在的你很critical,是从根本处去说香港的过去发生了甚麼事。这些想法酝酿了很久,还是来到北京才出现的?
陈︰ 那「衝动」是长时间的,但后来一边写一边整理,有时是写了一些才想出来的。我想把自己的经歷整理好,将从前有趣但含糊的地方写出来,如此自己也会比较清楚 一点。从前在香港,我写过很多没人看的东西,但你没可能依靠写些没人理会的东西维生,所以转了做一些比较有反应的工作,例如写电影剧本,至少有钱收。结果 我也走了不少不同的路,如今才决定纯粹写作。
梁︰ 2000年来北京的时候,你已打算要写小说?
陈︰ 对,一直想写小说,关於大陆的题材。但就是写不出来。你青少年时期不在大陆生活,根本写不到。每次我开始写了一点东西,便会心虚,因我不太知道那些人是怎样活的。直至08年有西藏事件、四川地震及奥运,我才看清楚要写的是一个盛世。
梁︰ 中国一直变得很快,既有很多乐观的期望,也有很多灰暗的东西。但究竟怎样命名这种状态?很难。它变得太快,很难捉住。
陈︰ 捉不住,定不到型。08年便可以了,特别是西藏和抢火炬的事发生后,你看到年青人变得很清楚了,开始了另一个新世界,他们有了态度。今年更不用说,西人也在说中国盛世。
梁︰ 上两星期Newsweek的主笔Zakia写了一篇东西,说金融风暴里中国是唯一的赢家,今期的Times封面用了中文「五」这个字作背景,主题是「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的五件事」。近来我看参考消息,所有的外电翻译都在说中国有多厉害。
陈︰ 2000年还在讲中国可能会崩溃,经济方面不行,现在都没人说了。2000年香港及台湾人肯定也觉得自己是先进的、发达的,中国是落后的。不知从何时起,中国变成领先的,我们不太行。
梁︰ 為何你选择以一个像科幻或幻想小说的形式去写《盛世》?
陈︰ 我觉得自己想说的东西还不够清晰。若我把它推至2013年,那便可以更夸张一点,整个趋势也会更清晰─那时中国会比现在更强、更富、更自信。所以《盛世》 其实是关於现在的,这个故事是说现在的中国,我只是把时间推迟了一点。这个未来跟现在相差无几,只不过我们用放大镜把现在的事放大一点,我希望做到这件 事,告诉其他人中国正走向一个更强、更富的盛世。
梁 ︰ 这就是这本书让我最好奇的地方,你的选择很奇怪。最初我看的时候,觉得它就像《美丽新世界》和《1984》。中国60年来没一本反乌托邦的小说,我常常问 一些大陆作家,我们有很多「反动」小说,但没一本写得像《古拉格群岛》,而写dystopia的更加没有。我一看你这本书,便知道你是走这条路线,但若真 的是这样,又有几件事是不成立的。第一,那时间太近,近得不能构成一个很大的幻想元素。所以我猜这是个刻意的设计,因為它的时间太近了,2013年一下子 便过去了。这是刻意设计一个不长不短的时间,是一个以目前现实可以合理预测的推演结果。
另一方面,它的科幻程度很低,当中的人物都很实在,有些影射作用,这些人物即使不是任何一个具体人物,你也会觉得他们的形象很清晰,像你曾经在哪里见过这些人。譬如说方草地那种人,还有与他一起的张逗、小希,是有这麼一类人明显经过六四。
陈: 这些人物当中是存在着一种真实性的,当然我也希望大家在读的时候会enjoy,我希望它能够是本可读的小说、好看的小说。因為当年的反乌托邦小说像《我 们》,其实是相当乾涩的。我借用了一点点政治小说、反乌托邦小说和推理小说的手法,它带点悬疑,各个类别也有一点点。当中的人物那麼多,故事有那麼多条 线,可却没甚麼结尾,有点像Zadie Smith的《白牙》(White Teeth)。我受了她影响,将人物和处境丰富化了,而非单纯的将一个论点写出来,尽量有多点声音,一种混杂的声音,让各种人将自己的观点说出来。那会比 较能够说出中国的复杂性。其实我并没有特别的定论在里头,不是说我必定要说出某种感觉,说整个中国就是如此。
小说的包容量很大,可容许你说很多的东西,那是论文、评论所无法做到的。我在2005年替台湾《思想》杂誌写了一篇长文,评论当时的一本书《歧路中国》, 我用了「絳树两歌」的比喻,讲到若要说中国的好,你会说不完;要说中国的坏吗,也会说不完。但现在的问题是,它比两歌更复杂,不只是好与不好,那种心境的 转变是多样化的。絳树一张嘴可唱两首歌,但原来两首歌还是未够的,要同时唱几首歌才行。是很难作评论的,所以我尝试用小说。
我一边写一边想人物角色。我2000年来了北京以后,特别是我的女友于奇的朋友圈子内,大概有一半都是公共知识分子,这是我身边最熟悉、最大的一个圈子。 近八、九年,我跟从前工作的传媒、娱乐圈、电影圈及文化杂誌那些朋友,反而来往少了。现在来往最多的是公共知识分子,我常常听他们说话,那些事我没地方插 嘴,但我感觉到他们思考的范围是甚麼。这一个小说,就是写这个圈子的人。
梁 ︰ 其中一个最令人心痛的角色是韦国。因為现在有很多这种年青人,觉得自己是精英,一方面很真诚地相信某些价值,觉得去中宣部工作是一件很浪漫的工作;但另一 方面,他又充满了机心、计算;是两种东西的结合。一方面是一个有一丁点理想,真的相信国家前进,另一方面是一种个人功利的极端计算,是两者的结合。
陈: 这的确是我自己的感觉,大陆的年青精英,的确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因為他们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之下,深知需要在某些时候说假话,在某些时间要做一些经营的事, 然后才能爬上去,所以他们是内化了这套东西。同时他们又觉得自己生在一个很好的时候,亦很相信官方话语,大部分的官方话语,他们根本不太愿意去挑战,他们 希望去相信自己是活在一个好的时代、一个有作為的时代。上一辈再苦难,也不关他们的事了。我经歷过一次饭局,李慎之也在场,竟然当场跟一个年青作家吵架。 年青作家觉得李慎之真的很多餘,还在说这样的老话,常常抱怨,他说现在有甚麼问题呢?现在有多好等等。他就是这样跟李慎之吵架,完全是没大没小的,旁边的 人看在眼里,都呆了。李慎之又是很认真的人,竟然也真的跟那年青人吵。
梁: 有趣的是,这群年青人即使知道了一些被官方史学掩盖了、扭曲了的歷史真相,也觉得不太要紧。
陈: 对,他们甚至觉得扭曲是正常的。同时他们在面对一个很大的竞争,他们亦很懂得去操作,很知道怎样去得到较好的位置,例如入党,现在是一件很盛的事。
其实入了党是不是真的有帮助,不一定,他就当多买一个保险。但入党后会要你检讨自己,所谓检讨自己,就是供出身边的人,说他们做错了甚麼,然后知道了这些 是错的,之后自己就不做。就是把身边的人的反动、反党行為说出来,他们不觉得这种告密行為是一回要事。可能他们觉得上行下效,你们都可以做,為甚麼我们不 能做?这变成了已接受的道德底线。但同时我也碰到一些真的很精英、很厉害的才子,他们真的很精英主义,觉得精英应该掌握所有的控制权,还说中国传统就是 「士」,简直觉得人应该分等级。
梁: 新中国在建国的时候已经根深柢固地埋伏了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最喜欢说的口号是「落后就要捱打」,对吧?如果你这样理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係, 你很容易在内部也是这样理解,所以中国的市场竞争比其他地方更赤裸、更无情。因為我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太强。另外,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盛世》的气氛描 写,就是那种盛世的感觉,那一种自我中心的气氛是很可怕的。例如我前日在一个沙龙介绍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有一个中科院年青人走来跟我说:「全球暖化是一个 西方发达国家的阴谋,用来箝制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梁老师你不要只说西方的观点,也要留意一下我们这些中国的观点。」我心想,这是甚麼中国观点啊? 全球暖化,你以為人家是廿多年前想这些点子出来害我们中国吗?阴谋论也要有一个怀疑的根据,人怎麼会这样思考的啊?
陈: 这也是很常见的,他们说甚麼也被西方影响了。现在体制吸纳了精英,精英也背靠大国。现在中国的学者也背靠大国,他们的思想开始改变得很厉害,他们知道自己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在支持。
梁: 其实这个制度是令很多人得到满足的制度。譬如一个中国学者,他已经厌倦了再去做一个二流国际地位的学者。他想做一个国际级的大师,可能出发点就是我们中国 人想到自己的一套,是跟你们不一样的,大家可以平起平坐,我甚至比你更厉害呢。这不只是一种向官方献媚,而且包含了一种作為一个学者的某种尊严的追求。而 你所说的背靠大国,就是这个制度令一些像韦国的精英得益,他又能替国家得益。对学者来说也一样,国家在他身上得到好处,他本身也得到好处。
陈: 大国的确是有分别的。如果我写一个小说讲今天的香港,反应肯定差得远了,因為大家现在都对中国有兴趣。
梁: 你还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就是大胆预测了中国模式到底是甚麼。我看《盛世》看到后来很错愕,想不到小说最后是像这样子的演讲,使我觉得你在用一个小说的形 式去表达一个社会评论。而且这一个评论包含了某些预测,例如说在经济上中国怎样摆脱了令全世界进入「冰火期」的困境。
陈: 这的确是我自己觉得可能的一个现实。不过它多数也不会是这样子发生的,因為西方不一定发生冰火期,中国也未必能那麼完美地执行一套计划。我只是觉得有这个 跡象,例如日本跟中国的发展,是比我想像中快。我写书的时候,东亚共同体是没有人提及的,现在就突然有人提出来了,以前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未来甚至 连农村问题也得到缓解,因為经济好了、收入多了,资源能转付农村,所以消解了很多农村的矛盾。中国现在的资源、能力可以应付很多局面。如果这个乱是因為全 世界的经济不景而引起,可能也不是一件大事,因為中国人不会全怪到政府上头,只会觉得祸是美国搞出来的,大家也只是骂美国。所以这样的一个盛世我觉得真有 可能会出现。中国可趁机会增强,就像这一次的金融风暴。
梁: 书中那神秘消失的一个月更妙,因為是幻想小说的格局,读者一定会以為是政府下了药,令大家失忆。谁知道原来是人民主动去忘记了那一个月。这个月的消失一方 面很可信,另一方面又很令人寒心,就是因為我们也看到了六四是如何从记忆中消失的。虽然其他事已做得这麼好了,可是这个政府有些本质性的东西没有改变,基 本上仍是一个专制。
陈: 你提得对,六四就是了。另外,由89年到92年南巡中间还经过一个寒冷期,可是已经没有人记得,明明是这麼近的事。改革开放后,83年甚至还有过很厉害的严打。
梁: 对,那时候是打流氓。我记得我昨晚才听一群娱乐界的人在说,现在的狗仔队流行偷拍谁人车震。哗,这些东西要是换作83年严打的时候是流氓罪呀,可能会死刑的,但也没人记得了。
陈: 他们已经完全忘了这些事。但这些事随时会再回来。这一次我书里有场很强的严打,用作一个专政的比喻。我们害怕的专制独裁就是对某一个阶层的人可以随时严 打。其实中国自49年建国以来有很多次不同形式的严打,只是有一些我们不叫严打而已。甚至四清运动或是法轮功,也都是对某一阶层的严打。严打是超越了法律 程序,是人权没保障的时候,是国家权力变得绝对、可以滥用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冤案,有很多人枉死。但这些都是一定可以再发生的,其性质没有变。所以我很 强调把严打定义為一个专政的标誌。
梁: 你在书中写到像何东生这样的官员比较令人疑惑,一个高层的官员会不会是一个这样的人呢?
陈: 我觉得如果写一个贪官污吏就没意思了。你捉一个这样的人来说甚麼呢?我觉得我要写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官员,而且基本上不是一个很差的官员。不见得他完全不曾 贪污,因為他也供小孩出国读书,但他基本上仍然是想好好的干一些事。就算他基本上是一个共產党官员,他是在想共產党的棋应该怎样走,政权应该怎样保证,然 后同时令中国进步。
梁:但当初的问题你还未解决,就是為甚麼你最后会用何东生演讲的方法去结局呢?
陈: 其实这才是我最初要写的东西。我最初就想好了,我要写多声道的当代中国,可以开很多不同的channel,但很难去开一个channel给中国的高层官员 去逼他们说话啊。就算是在真实世界,他们也不会这样说。他可以跟谁说?他带到棺材去也没机会说出来。那些政策连讨论也不可以,又不能跟家人说。如果不用小 说,又怎可能做得到呢?只可以用一个小说的方法,去令不同的声道同时并存在一个文体里面,而且有些东西你是要强制他说,你不强制他就不会说了。所以我在小 说中捉了何东生,跟他做了一个交易,如果他不说真相就会死,而他还要吃了药,说多了。否则这个声音永远是缺席的,我们永远不知道官员们在想甚麼。
梁: 除了严打,另一表现出专制的地方就是在水里下药,让全国人民都有点high。
陈: 这个当然是隐喻,就是中国人人都很high,人人都有很多大计,要做一些很伟大的事,搞各种很大型的活动。尤其是我碰到的精英阶层,他们有很多资源在手,会想更多的东西。
梁: 大家一high,老唱反调的自由派就消声匿跡了,《南方周未》倒闭、万圣书园关门。你想像的未来很可怕。
陈: 最糟的是有些人不是给政府打倒,是他们失去了市场,年青人态度改变,对西方的兴趣降低,都认為不用听西方的话了。而自由派一定代表亲西方吗?其实也不一定。但他们有一些话语被认為是西方话语,这是个硬伤,使人觉得你们一定是帮西方的。
梁: 但身為一个香港人,写大陆的东西经常会被人质疑你的资格。
陈: 对呀,香港人的确不够理解大陆,所以我一直不敢写,直到我觉得自己对这个题材和这批人有足够的理解。但写出来都要经过考验,要给他们看看有没有真实感,感 觉方面是否正确。幸好我女友于奇一看便会知道哪些对,哪些错。我的写作一向是由她去看,然后我再作出修正。她的feedback很重要。那是一个文学上的 真与假,而非歷史上有没有发生,她能够判断得到。这次我够胆去写是因為于奇在,她能够替我看稿子。但话说回来,大陆作家需要考虑的问题多很多,可能他们会 选择的写作策略是魔幻,或写迂迴一些的东西,但不会这样直接,例如他们不想在小说里提到八九六四;但我们可以不用避忌。
梁: 你接下来会再写甚麼?
陈: 我是想再写小说的,或者多写一本别的,但也是和大陆有关的东西。
梁: 继续藉「盛世」去发挥?
陈: 会有关係,但不会是同样的主题。现在正在构想中,但那不会是个续集,我不会再写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圈子了。这一年我其中一个重点是去一些三线地级市看看,西北、西南、安徽、江苏北部等等平时人们不会去的地方。
梁: 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写香港的。就等於过去我们说上海的衰落,现在可能你目睹了第二个上海的衰落,那就是香港了。你曾经歷过她所谓的heyday,你曾参与其中的荣景……
陈: 我觉得你可以有足够想像去写这个,你有这个情怀。我现在整个人都去了大陆,已无法扭回香港。写一些以香港作背景的短篇小说可能还有机会,但若是用一个大故事去说香港,恐怕我写不到了。
我读的时候一直以为陈冠中是画家--后来想起来把他和吴冠中搞混了--看着看着觉得不对劲,反应过来好象看过一篇梁文道采访他的文章。
梁文道采访陈冠中
http://commentshk.blogspot.com/2009/12/ ... _5479.html
从 前我一直都说不準陈冠中的形象。最早他是全华文世界第一个写专书介绍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冷门作者,后来创办《号外》引领城市文化风潮,再后来他写电影 剧本、管理唱片公司……你实在不知道该用哪一套习见的角色去定位这个人。就像我的旧上司梁浓刚,一方面研究拉康,另一方面在电视台任职高层。也许那一代香 港文化人就是这样,见多识广,游歷丰富,但却不太张扬,无论干了多少也许很值得称道的功业,最后都总是好像甚麼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 自从陈冠中定居北京之后,我们对他的印象反而清晰了。原来他始终是个作家,一个锐利的作家。几年前,他开始有系统地书写香港,其自省之深足令不少他的同代 人汗顏,开啟了香港集体反思的精神运动。现在,他以城市观察者的身分,终於交出第一部谈论中国大陆的小说。无论你喜不喜欢,赞同或不赞同《盛世》里的未来 愿景,你都不能否认它的确看得人冷汗直流。谁也猜不到这麼多年之后,竟是一个香港人率先写出中国版的《美丽新世界》。
我在北京和陈冠中聊他的新书,但不免还是要从香港说起,譬如说香港文化感性中那股独特的「冷」。
梁︰ 梁文道
陈︰ 陈冠中
梁︰ 不知道為甚麼香港的sensibility会这麼cool?
陈︰ Cool的确是最贴切的字,香港不喜欢sentimental,不喜欢滥情。
梁︰ 譬如说进念那种剧场,台湾不会有,大陆也不会有。香港很多artist,做installation和行為艺术做了这麼多年,但是从来没有好像大陆这样一做就沸沸扬扬,就让人觉得厉害,觉得是世界第一。这到底是為甚麼呢?
陈︰ 而且就算是很重的一个题材,也要做得轻一点,也要将那个主题说得小一点。我觉那真是某个阶段的西方品味,譬如说五、六十年代欧洲那种存在主义的 品味,或者是后来结构主义与美国的counter culture品味,是cool的,是冷调一些的,就是不喜欢说一些激情大主题,不喜欢激情到连自己也感动。起码我自己就是,整天都想用最简约的方式去说 很多事情。
梁︰ 昨天在我一本书的朗读会中,一位读者就选了一篇我写的东西来读。但我自己其实不太喜欢那篇东西,因為当时我的写作策略是在西藏问题闹得最激烈的时候,特地用很温情的东西去说服一些愤青。我非常不喜欢这种方式,因為它根本不像我,可是有些读者却很喜欢,很奇怪。
陈︰ 大陆的官方论述也永远是华丽的,带感情的,句子和用字都很讲究,就算是中央台的晚会,那些主持人出来说的话都是漂亮的。其实那都是套句,陈腔滥调。这可能是一个训练。即便台湾,比起香港也多了很多感情,香港是特意将感情元素削减了。
梁︰ 台湾很强调一种很温暖、很sweet的东西。譬如他们的唱片,那些印有歌词的小书根本是放不进去CD盒,因為它太厚了,每一页都要有歌者在上面用手写下自己在录这首歌时的心情如何如何,我们香港人看了就会说,有没有搞错。
陈︰ 香港的作家多半也比较cool,由刘以鬯到西西皆如是。就算西西有点童真,有点朴素;或者后来的黄碧云比较「激」,但就是没有那种温情。
梁︰ 所以在这两者之间,香港才有了一个特别的文化的感性存在。这种感性很世故,乃至於我们的电影没有很多温情戏,寧愿喜欢「笑爆咀」,苦中即时求乐。
陈︰ 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已很害怕,不是怕,而是已经开始会去嘲讽「文艺腔」,去拒绝这种东西。起码我自己成长、写作的时候,就很害怕给人说是「文艺腔」。於是这 个「文艺腔」的传统就在香港被切断了。我们又怕被人认為是「扮嘢」,寧愿「存真」也不要「扮嘢」,总之就是不想世界太浪漫,我们对浪漫本身就有疑问,香港 人并不浪漫。我们更不喜欢那些自怨自艾,然后觉得自己很悲惨的情感,譬如说台湾的「悲情」和大陆的「百年国耻」。
梁 ︰ 所以当台湾一份刊物叫我写四九年的香港时,我才发现香港相当有趣,很多人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很惨很失败,我们在香港住了这麼久,你何时听过香港人会这样说? 所以龙应台那本书,就只有台湾人才写得出来。你父母那一代从上海逃来香港,他们会不会常常这样喊苦?没有呀。我认识很多人都是由大陆下来,而且当年还真 苦。但问题就是他们从来不讲,也从来不会拿这些事来说,更不会将这件事变作一种cultural element。
陈︰我父母那一代都好像没有太强调那种苦。他们不会当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整天围绕受害者这个主题,然后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生怎麼会这样苦。我们很快就可以转 换心境。我记得小时候他们有讲过香港是一个福地,说香港真的很好。他们都有一个比较的想法,起码与在大陆的朋友和亲戚的遭遇不同,他们都向前看,很乐观, 然后急急要「搵食」。
梁︰ 台湾是外省人觉得自己很惨,流离失所;本省人也觉得自己很惨,受人压迫。香港人就很少觉得自己惨,反而会觉得自己很幸运。话说回来,你是不是到了北京之后,才更加醒觉香港特别的地方?所以《我这一代香港人》和《什麼都没有发生》都是你到了北京之后才动笔的,对吗?
陈︰ 是,这都是到了北京之后才动笔的。但我觉得那个源头是在七十年代尾,忽然之间自己有一个香港的意识出来了,譬如突然之间怀旧,那究竟要怀念甚麼呢?七十年 代尾怀旧,是想起六十年代自己十多岁时成长的过程。其实那不是很多年后,就在怀念自己十多岁的日子。另外就是觉得香港是我们的家,所以要说说香港。那一种 衝动是最重要的。
梁︰ 那就是办《号外》的时候?
陈: 对,办《号外》的时候。譬如说当年看Q仔(黎则奋)写湾仔,我也觉得很震惊,他把湾仔说得这样有趣。我就觉得,对啊,我们自己的地方也很有趣,那个震惊是 很大的。但是,虽然有了这个意识,却没有去整理它。真的事后回头再看,就是来到了北京才去整理。我92年开始进来,才有一个大的比较去感到大陆与香港的反 差,然后在97年前后开始写《什麼都没有发生》那本小说,连名字都是有比较之下才知道,原来自己长大的地方可能是⋯⋯用文学的语言来说,就叫做「什麼都没 有发生」。
梁: 那是很cool的。
陈: 很cool,相比起台湾和大陆的同龄人来计,如果没有比较就不会想到这一点。这种东西现在想起很幸运,也很平淡。相对来说,我们的经歷是比较平淡。譬如说在大陆,我是属於老三届的。
梁: 你办《号外》的时候有一个很清晰的城市文化意识,对吗?
陈︰我自己觉得《号外》有两个源头,首先是因為去了波士顿,看到当时美国的那个counter culture的「水尾」,就是越战差不多完结,嬉皮士开始淡出,气氛开始静下来的时候。我记得75年我离开波士顿前,刚刚开了一些很新的Disco,一 个享乐年代回来了。我心想,哗,為甚麼会这样?我们前一阵子还在说要对抗越战,还要与政府抗衡,怎麼现在忽然在跳舞?Counter culture是不跳舞的,起码不跟音乐跳,除非你是拉丁人或者是非洲裔,我们当时眼中就只有白人是没有Disco culture的。74年哈佛才有一个大型庆祝会庆祝越战结束,跟着忽然之间就开party跳Disco了。那时候有一些地下报纸,特别是波士顿有The Real Paper,The Phoenix,纽约则有Village Voice。甚麼趣味的都有,很适合我们自己的趣味,从左翼政治到饮食和青年人的生活,包罗万有,然后有很多年青一代才懂得欣赏的幽默,有自己的漫画。我 觉得这种事情我们应该做。
但香港其实是做过的,六十年代的《中学生周报》、《年青人周报》,七十年代的《七○双周刊》,其实都是这类型的东西。然后在七十年代中,忽然之间这种以整 代人作為对象的刊物全部「死掉」,《七○双周刊》已结束,《中学生周报》也结束了,《年青人周报》是硕果仅存,可能还有一两份在喘着气,但最后在76年办 《号外》之前就都没有了。
但我觉得我懂得做,能够编一本这样的东西,能做到美国的那种感觉。所以起初是很模仿西方的,因為那时候比较崇拜英美。当年他们那些小报都叫做「tabloid」,所以我们就叫做《号外》,一开始做了五期双週报,就像是地下报一样。但因為发行太困难,所以才改做杂誌。
梁︰ 当时你们是否都很有意识要说香港的事情?
陈︰ 这反而是迟一些才出现的。我们起初是讲英美,以大学和大学毕业生等年青人喜欢的题材為主。我们对输入新潮洋文化最有兴趣,就是在别人未说起之前,我们先 说,然后才说回自己的成长过程。我们说香港不是由开埠说起,而是从五、六十年代说起;邓小宇的记忆可能去到五十年代,我的记忆可能去到六十年代中段的《中 学生周报》。再加上我们知道成长阶段比我们稍為大一点的人,例如唐书璇这一类。
这两种东西吸引到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很多是刚由外面回来的人。我们那一代出道了,读完书回来了,很多在外国学过一些奇奇怪怪的事物,发觉我们的杂誌会介绍 这些小眾的东西,所以他们会聚过来一起做。譬如有次我们写到一些关於同性恋的东西,可能我们的态度写得比较好,立即有人来和我们接洽,表示想替我们写文章 和替我们做点事情,后来就开了一个专栏,叫「少数权利」,其中一个activist叫小明雄。还有一个做时装的朋友刚从加拿大读完书回来,说自己想替我们 编一些时装的内容。当时走过来的全部是同代人,大家集合起来,只不过因為当时我们提供了一个平台。
梁︰ 你们一整代的Baby Boomer留学回来了。
陈︰ 那是第一代的Baby Boomer回来,刚刚开始佔有了一点位置。我们最早的广告都是有一些boomer加入了一些公司,拿到一定位置,然后可以给我们一些广告。在八十年代 初,如果掌权的是个30岁左右,在外国读design回来的,他就会将那些广告先给我们,又或者找我们的杂誌去写一点东西。另外当时有一群人,到底是理工 还是大一设计学院出来的,我都已经忘记了,反正都是学美术的,他们成立了一个「插图社」,对设计很发烧。他们自动跑来找我们说︰「不如让我们替你做封 面。」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力量,而且全部都没有收钱。
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為我们当时没有鲜明旗帜,现在我才想到这事情。如果像是《七○双周刊》这样有一个鲜明的意识形态,也可以聚到一群人,但会是另外的一群。反正《号外》的旗帜不鲜明,就连创刊号都没有发宣言就开始了。
梁︰ 為甚麼会这样?為甚麼会没有创刊词?
陈︰ 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但我连杂誌也不肯储存,我觉得过了就算,没有甚麼大事要说,我们喜欢做甚麼就做甚麼。
梁︰ 这真的「很香港」了。
陈︰ 没错,我们连宣言也不肯写。因為当时我在美国学新闻,有一个新闻记者的态度,但我不肯讲一些很大的态度,譬如先讲一下甚麼关怀呀,完全没有,反而整天都当「知识分子」四个字是搞笑的,更不肯叫自己做知识分子,把它当成是取笑老一辈的字眼。
梁︰ 你现在这种对於《号外》的描述,是不是在你来到了北京之后,回想起才更加清晰?
陈︰ 是,现在就更加清晰一些,但是当初也的确知道,总之见到有趣的,就会把它放进去,见到新的东西也要放进去,时髦的更要放进去。我所谓的「时髦」是我自己心 目中想做的事情。就好像发现一个人很有型,他叫荣念曾,為何他穿的衣服这样阔?那时候大家很流行穿窄衣,他就去穿阔衣,还穿一身黑色的阔衣,这样很有型 呀,原来他从纽约回来,我就决定一定要拉他过来,无论他做甚麼也要给他大篇幅。其实真是没道理,我根本就不认识他所做的范畴!就是这样,我们没有甚麼胸怀 大志,要做些甚麼大东西出来的宏愿。
梁︰ 所以后来大家都说《号外》是华文世界第一个城市文化杂誌,其实你们当时根本没有去想这回事。
陈︰ 没有。用「城市」这个字,只是觉得它很有趣。我们最初由Village Voice的原型开始,也参考了《中学生周报》、《七○双周刊》,但它们在消费文化那一面都是比较弱的。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中,美国又有一些新杂誌出来了, 例如讲glamour的有Andy Warhol的Interview,於是我们就学了一些Interview的做法。后来又有份叫New York的真正city magazine,全都是说纽约的有趣东西,我们一套上去,又发现香港也可以这样做,於是我们的副题就叫做「城市杂誌」。
虽然如此,但这个概念当时在商业上是不成立的,整件事没可能成功,但是一直说要结束也没有结束,起码有五次决定要结束,但每次有人肯「夹钱」,又有人肯投 资。好像林秀峰,后来是最大的投资者,但我们不认识他,是他主动打电话来说想投资在我们身上。然后这样子又再捱下去,捱到广告名人施养德进来,说要将杂誌 变得更大,更改版面,使设计变得愈来愈重要。其实之前我根本不知道甚麼叫设计,因為Illustration Workshop,因為施养德,我才知道这是设计。
儘管如此,但那时杂誌的生意还是不行的,直至美国新闻界创作了Yuppy这个字。因為有了Yuppy这个字,於是就有Yuppy產品;当Yuppy產品来 到香港,香港的广告公司便问香港的Yuppy媒体在哪里?而那时全部广告公司都不知道甚麼叫Yuppy,只知道有一份很奇怪的杂誌叫《号外》,那麼乾脆把 《号外》当作Yuppy吧。自此之后就有很多广告了。回看起来是有一点幸运,不然就捱不了那麼久了。
梁︰ 你也挺幸运的,在每一个地方也赶上有趣的时刻。在波士顿时,是某种文化运动的尾声;然后在台北呢,你度过了最有活力的时候,就是戒严前后。
陈︰ 做电影是戒严前,做《号外》就是戒严后。
梁︰ 后来你去台北住,正好碰上了台湾文化出版界和文化发展最鼎盛的时期,对吧?
陈︰ 是很鼎盛。94至00年我长住台北做有线电视,恰巧是李登辉当上了总统,但未经正式民选,民进党跟国民党吵得最厉害的时候。
台湾发展得很快,94年杂誌已做得很好,书也很蓬勃,甚麼都已经有人做了;有人研究最激进的性解放,很多人写同志,地下的有《破周刊》,有高有低甚麼也 有。台湾在九十年代后的文化是十分完整的,引进外国的东西要比香港做得好,各种各样新的思潮也有人谈论,文化界的地位也比香港高,所以在94至00年间我 写得很少,因為在台湾甚麼也有人写。旧日我能够写东西,许多时是因為没甚麼人写,我觉得我不写,便没人写了。虽然我不是专家,也略知一二。
但我反而在台北写了一本书,是电视剧本,叫做《总统的故事》,后来皇冠把它当作影视小说出版。原本我们打算拍李登辉的故事,请了张大春写十集,平路写十 集,希望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去写,因我知道他俩的态度有点不同。结果二人都写不出来,张大春没时间写剧本,写了个《撒谎的信徒》,但那没可能拍得出来, 因為它不只是谈李登辉;平路一样也写不出来。原来在94至95年,写李登辉是很难的,那怎办?要拍了,於是我自己写了十集出来,由赖建国当导演拍成电视 剧,但后来决定不播了。就因為这样,我下了不少工夫,反而有助於我理解台湾。要从日治时期开始探讨台湾人為甚麼会视李登辉為台湾之子。也许太近了,所以张 大春和平路写不出来。我作為外人反而比较好。
梁︰ 然后你又到了北京。
陈︰ 2000年,别人的时代已超越了我们的。我到大陆,是想做一点网站的东西,怎料人家网股也爆了,阿里巴巴和QQ又已经开了,我还能做甚麼呢?另一方面,《时尚杂誌》集团也在,同时还看着七九八一直旺。后来我乾脆甚麼都不做,写东西算了。
梁︰ 所以香港人在2000年才来北京发展,想打一个庞大的事业是没可能的。
陈︰ 现在的门槛更是太高。我们没甚麼优势,没甚麼比人叻。旧时叻,是因為整个社会走得前一点,你只要跟着自己社会的步伐,便会比人走得快一点点。内地在92年 时和我们有很明显的差距,我记得当时做唱片,根本不宣传,只要找记者写点东西,便卖到不得了,就是这样容易。
梁︰ 你在《号外》时期写的东西跟现在的不同,现在的你很critical,是从根本处去说香港的过去发生了甚麼事。这些想法酝酿了很久,还是来到北京才出现的?
陈︰ 那「衝动」是长时间的,但后来一边写一边整理,有时是写了一些才想出来的。我想把自己的经歷整理好,将从前有趣但含糊的地方写出来,如此自己也会比较清楚 一点。从前在香港,我写过很多没人看的东西,但你没可能依靠写些没人理会的东西维生,所以转了做一些比较有反应的工作,例如写电影剧本,至少有钱收。结果 我也走了不少不同的路,如今才决定纯粹写作。
梁︰ 2000年来北京的时候,你已打算要写小说?
陈︰ 对,一直想写小说,关於大陆的题材。但就是写不出来。你青少年时期不在大陆生活,根本写不到。每次我开始写了一点东西,便会心虚,因我不太知道那些人是怎样活的。直至08年有西藏事件、四川地震及奥运,我才看清楚要写的是一个盛世。
梁︰ 中国一直变得很快,既有很多乐观的期望,也有很多灰暗的东西。但究竟怎样命名这种状态?很难。它变得太快,很难捉住。
陈︰ 捉不住,定不到型。08年便可以了,特别是西藏和抢火炬的事发生后,你看到年青人变得很清楚了,开始了另一个新世界,他们有了态度。今年更不用说,西人也在说中国盛世。
梁︰ 上两星期Newsweek的主笔Zakia写了一篇东西,说金融风暴里中国是唯一的赢家,今期的Times封面用了中文「五」这个字作背景,主题是「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的五件事」。近来我看参考消息,所有的外电翻译都在说中国有多厉害。
陈︰ 2000年还在讲中国可能会崩溃,经济方面不行,现在都没人说了。2000年香港及台湾人肯定也觉得自己是先进的、发达的,中国是落后的。不知从何时起,中国变成领先的,我们不太行。
梁︰ 為何你选择以一个像科幻或幻想小说的形式去写《盛世》?
陈︰ 我觉得自己想说的东西还不够清晰。若我把它推至2013年,那便可以更夸张一点,整个趋势也会更清晰─那时中国会比现在更强、更富、更自信。所以《盛世》 其实是关於现在的,这个故事是说现在的中国,我只是把时间推迟了一点。这个未来跟现在相差无几,只不过我们用放大镜把现在的事放大一点,我希望做到这件 事,告诉其他人中国正走向一个更强、更富的盛世。
梁 ︰ 这就是这本书让我最好奇的地方,你的选择很奇怪。最初我看的时候,觉得它就像《美丽新世界》和《1984》。中国60年来没一本反乌托邦的小说,我常常问 一些大陆作家,我们有很多「反动」小说,但没一本写得像《古拉格群岛》,而写dystopia的更加没有。我一看你这本书,便知道你是走这条路线,但若真 的是这样,又有几件事是不成立的。第一,那时间太近,近得不能构成一个很大的幻想元素。所以我猜这是个刻意的设计,因為它的时间太近了,2013年一下子 便过去了。这是刻意设计一个不长不短的时间,是一个以目前现实可以合理预测的推演结果。
另一方面,它的科幻程度很低,当中的人物都很实在,有些影射作用,这些人物即使不是任何一个具体人物,你也会觉得他们的形象很清晰,像你曾经在哪里见过这些人。譬如说方草地那种人,还有与他一起的张逗、小希,是有这麼一类人明显经过六四。
陈: 这些人物当中是存在着一种真实性的,当然我也希望大家在读的时候会enjoy,我希望它能够是本可读的小说、好看的小说。因為当年的反乌托邦小说像《我 们》,其实是相当乾涩的。我借用了一点点政治小说、反乌托邦小说和推理小说的手法,它带点悬疑,各个类别也有一点点。当中的人物那麼多,故事有那麼多条 线,可却没甚麼结尾,有点像Zadie Smith的《白牙》(White Teeth)。我受了她影响,将人物和处境丰富化了,而非单纯的将一个论点写出来,尽量有多点声音,一种混杂的声音,让各种人将自己的观点说出来。那会比 较能够说出中国的复杂性。其实我并没有特别的定论在里头,不是说我必定要说出某种感觉,说整个中国就是如此。
小说的包容量很大,可容许你说很多的东西,那是论文、评论所无法做到的。我在2005年替台湾《思想》杂誌写了一篇长文,评论当时的一本书《歧路中国》, 我用了「絳树两歌」的比喻,讲到若要说中国的好,你会说不完;要说中国的坏吗,也会说不完。但现在的问题是,它比两歌更复杂,不只是好与不好,那种心境的 转变是多样化的。絳树一张嘴可唱两首歌,但原来两首歌还是未够的,要同时唱几首歌才行。是很难作评论的,所以我尝试用小说。
我一边写一边想人物角色。我2000年来了北京以后,特别是我的女友于奇的朋友圈子内,大概有一半都是公共知识分子,这是我身边最熟悉、最大的一个圈子。 近八、九年,我跟从前工作的传媒、娱乐圈、电影圈及文化杂誌那些朋友,反而来往少了。现在来往最多的是公共知识分子,我常常听他们说话,那些事我没地方插 嘴,但我感觉到他们思考的范围是甚麼。这一个小说,就是写这个圈子的人。
梁 ︰ 其中一个最令人心痛的角色是韦国。因為现在有很多这种年青人,觉得自己是精英,一方面很真诚地相信某些价值,觉得去中宣部工作是一件很浪漫的工作;但另一 方面,他又充满了机心、计算;是两种东西的结合。一方面是一个有一丁点理想,真的相信国家前进,另一方面是一种个人功利的极端计算,是两者的结合。
陈: 这的确是我自己的感觉,大陆的年青精英,的确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因為他们在这样的一个体制之下,深知需要在某些时候说假话,在某些时间要做一些经营的事, 然后才能爬上去,所以他们是内化了这套东西。同时他们又觉得自己生在一个很好的时候,亦很相信官方话语,大部分的官方话语,他们根本不太愿意去挑战,他们 希望去相信自己是活在一个好的时代、一个有作為的时代。上一辈再苦难,也不关他们的事了。我经歷过一次饭局,李慎之也在场,竟然当场跟一个年青作家吵架。 年青作家觉得李慎之真的很多餘,还在说这样的老话,常常抱怨,他说现在有甚麼问题呢?现在有多好等等。他就是这样跟李慎之吵架,完全是没大没小的,旁边的 人看在眼里,都呆了。李慎之又是很认真的人,竟然也真的跟那年青人吵。
梁: 有趣的是,这群年青人即使知道了一些被官方史学掩盖了、扭曲了的歷史真相,也觉得不太要紧。
陈: 对,他们甚至觉得扭曲是正常的。同时他们在面对一个很大的竞争,他们亦很懂得去操作,很知道怎样去得到较好的位置,例如入党,现在是一件很盛的事。
其实入了党是不是真的有帮助,不一定,他就当多买一个保险。但入党后会要你检讨自己,所谓检讨自己,就是供出身边的人,说他们做错了甚麼,然后知道了这些 是错的,之后自己就不做。就是把身边的人的反动、反党行為说出来,他们不觉得这种告密行為是一回要事。可能他们觉得上行下效,你们都可以做,為甚麼我们不 能做?这变成了已接受的道德底线。但同时我也碰到一些真的很精英、很厉害的才子,他们真的很精英主义,觉得精英应该掌握所有的控制权,还说中国传统就是 「士」,简直觉得人应该分等级。
梁: 新中国在建国的时候已经根深柢固地埋伏了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最喜欢说的口号是「落后就要捱打」,对吧?如果你这样理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係, 你很容易在内部也是这样理解,所以中国的市场竞争比其他地方更赤裸、更无情。因為我们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太强。另外,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盛世》的气氛描 写,就是那种盛世的感觉,那一种自我中心的气氛是很可怕的。例如我前日在一个沙龙介绍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有一个中科院年青人走来跟我说:「全球暖化是一个 西方发达国家的阴谋,用来箝制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梁老师你不要只说西方的观点,也要留意一下我们这些中国的观点。」我心想,这是甚麼中国观点啊? 全球暖化,你以為人家是廿多年前想这些点子出来害我们中国吗?阴谋论也要有一个怀疑的根据,人怎麼会这样思考的啊?
陈: 这也是很常见的,他们说甚麼也被西方影响了。现在体制吸纳了精英,精英也背靠大国。现在中国的学者也背靠大国,他们的思想开始改变得很厉害,他们知道自己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在支持。
梁: 其实这个制度是令很多人得到满足的制度。譬如一个中国学者,他已经厌倦了再去做一个二流国际地位的学者。他想做一个国际级的大师,可能出发点就是我们中国 人想到自己的一套,是跟你们不一样的,大家可以平起平坐,我甚至比你更厉害呢。这不只是一种向官方献媚,而且包含了一种作為一个学者的某种尊严的追求。而 你所说的背靠大国,就是这个制度令一些像韦国的精英得益,他又能替国家得益。对学者来说也一样,国家在他身上得到好处,他本身也得到好处。
陈: 大国的确是有分别的。如果我写一个小说讲今天的香港,反应肯定差得远了,因為大家现在都对中国有兴趣。
梁: 你还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就是大胆预测了中国模式到底是甚麼。我看《盛世》看到后来很错愕,想不到小说最后是像这样子的演讲,使我觉得你在用一个小说的形 式去表达一个社会评论。而且这一个评论包含了某些预测,例如说在经济上中国怎样摆脱了令全世界进入「冰火期」的困境。
陈: 这的确是我自己觉得可能的一个现实。不过它多数也不会是这样子发生的,因為西方不一定发生冰火期,中国也未必能那麼完美地执行一套计划。我只是觉得有这个 跡象,例如日本跟中国的发展,是比我想像中快。我写书的时候,东亚共同体是没有人提及的,现在就突然有人提出来了,以前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未来甚至 连农村问题也得到缓解,因為经济好了、收入多了,资源能转付农村,所以消解了很多农村的矛盾。中国现在的资源、能力可以应付很多局面。如果这个乱是因為全 世界的经济不景而引起,可能也不是一件大事,因為中国人不会全怪到政府上头,只会觉得祸是美国搞出来的,大家也只是骂美国。所以这样的一个盛世我觉得真有 可能会出现。中国可趁机会增强,就像这一次的金融风暴。
梁: 书中那神秘消失的一个月更妙,因為是幻想小说的格局,读者一定会以為是政府下了药,令大家失忆。谁知道原来是人民主动去忘记了那一个月。这个月的消失一方 面很可信,另一方面又很令人寒心,就是因為我们也看到了六四是如何从记忆中消失的。虽然其他事已做得这麼好了,可是这个政府有些本质性的东西没有改变,基 本上仍是一个专制。
陈: 你提得对,六四就是了。另外,由89年到92年南巡中间还经过一个寒冷期,可是已经没有人记得,明明是这麼近的事。改革开放后,83年甚至还有过很厉害的严打。
梁: 对,那时候是打流氓。我记得我昨晚才听一群娱乐界的人在说,现在的狗仔队流行偷拍谁人车震。哗,这些东西要是换作83年严打的时候是流氓罪呀,可能会死刑的,但也没人记得了。
陈: 他们已经完全忘了这些事。但这些事随时会再回来。这一次我书里有场很强的严打,用作一个专政的比喻。我们害怕的专制独裁就是对某一个阶层的人可以随时严 打。其实中国自49年建国以来有很多次不同形式的严打,只是有一些我们不叫严打而已。甚至四清运动或是法轮功,也都是对某一阶层的严打。严打是超越了法律 程序,是人权没保障的时候,是国家权力变得绝对、可以滥用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冤案,有很多人枉死。但这些都是一定可以再发生的,其性质没有变。所以我很 强调把严打定义為一个专政的标誌。
梁: 你在书中写到像何东生这样的官员比较令人疑惑,一个高层的官员会不会是一个这样的人呢?
陈: 我觉得如果写一个贪官污吏就没意思了。你捉一个这样的人来说甚麼呢?我觉得我要写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官员,而且基本上不是一个很差的官员。不见得他完全不曾 贪污,因為他也供小孩出国读书,但他基本上仍然是想好好的干一些事。就算他基本上是一个共產党官员,他是在想共產党的棋应该怎样走,政权应该怎样保证,然 后同时令中国进步。
梁:但当初的问题你还未解决,就是為甚麼你最后会用何东生演讲的方法去结局呢?
陈: 其实这才是我最初要写的东西。我最初就想好了,我要写多声道的当代中国,可以开很多不同的channel,但很难去开一个channel给中国的高层官员 去逼他们说话啊。就算是在真实世界,他们也不会这样说。他可以跟谁说?他带到棺材去也没机会说出来。那些政策连讨论也不可以,又不能跟家人说。如果不用小 说,又怎可能做得到呢?只可以用一个小说的方法,去令不同的声道同时并存在一个文体里面,而且有些东西你是要强制他说,你不强制他就不会说了。所以我在小 说中捉了何东生,跟他做了一个交易,如果他不说真相就会死,而他还要吃了药,说多了。否则这个声音永远是缺席的,我们永远不知道官员们在想甚麼。
梁: 除了严打,另一表现出专制的地方就是在水里下药,让全国人民都有点high。
陈: 这个当然是隐喻,就是中国人人都很high,人人都有很多大计,要做一些很伟大的事,搞各种很大型的活动。尤其是我碰到的精英阶层,他们有很多资源在手,会想更多的东西。
梁: 大家一high,老唱反调的自由派就消声匿跡了,《南方周未》倒闭、万圣书园关门。你想像的未来很可怕。
陈: 最糟的是有些人不是给政府打倒,是他们失去了市场,年青人态度改变,对西方的兴趣降低,都认為不用听西方的话了。而自由派一定代表亲西方吗?其实也不一定。但他们有一些话语被认為是西方话语,这是个硬伤,使人觉得你们一定是帮西方的。
梁: 但身為一个香港人,写大陆的东西经常会被人质疑你的资格。
陈: 对呀,香港人的确不够理解大陆,所以我一直不敢写,直到我觉得自己对这个题材和这批人有足够的理解。但写出来都要经过考验,要给他们看看有没有真实感,感 觉方面是否正确。幸好我女友于奇一看便会知道哪些对,哪些错。我的写作一向是由她去看,然后我再作出修正。她的feedback很重要。那是一个文学上的 真与假,而非歷史上有没有发生,她能够判断得到。这次我够胆去写是因為于奇在,她能够替我看稿子。但话说回来,大陆作家需要考虑的问题多很多,可能他们会 选择的写作策略是魔幻,或写迂迴一些的东西,但不会这样直接,例如他们不想在小说里提到八九六四;但我们可以不用避忌。
梁: 你接下来会再写甚麼?
陈: 我是想再写小说的,或者多写一本别的,但也是和大陆有关的东西。
梁: 继续藉「盛世」去发挥?
陈: 会有关係,但不会是同样的主题。现在正在构想中,但那不会是个续集,我不会再写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圈子了。这一年我其中一个重点是去一些三线地级市看看,西北、西南、安徽、江苏北部等等平时人们不会去的地方。
梁: 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写香港的。就等於过去我们说上海的衰落,现在可能你目睹了第二个上海的衰落,那就是香港了。你曾经歷过她所谓的heyday,你曾参与其中的荣景……
陈: 我觉得你可以有足够想像去写这个,你有这个情怀。我现在整个人都去了大陆,已无法扭回香港。写一些以香港作背景的短篇小说可能还有机会,但若是用一个大故事去说香港,恐怕我写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