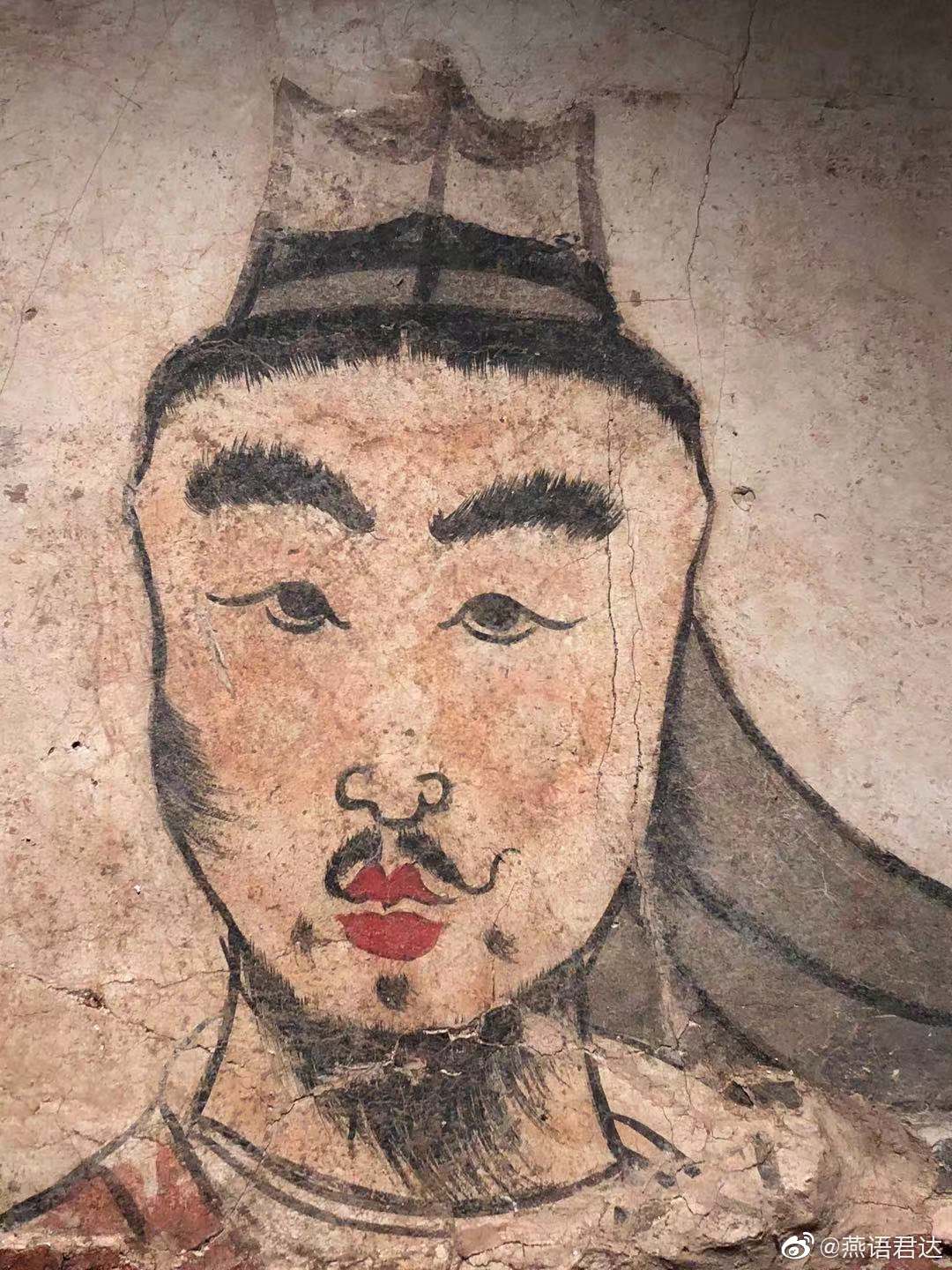上古至春秋战国
刚看了几页宫崎市定的中国史就笑出声来,他一上来就斩钉截铁地支持文化一元论,文明发源地为叙利亚,也就是现代考古学确认的 Fertile Crescent 地区。哈哈哈哈果然这是历史学主流,拒绝的“历史学家”除非能拿出大量旁证就是态度问题了。
宫崎教授的文风极其尖锐犀利,一点不客气委婉,说起凡事急于理论化抽象化的路线 versus 以事实为基础的历史研究方法,还说到科举教育出的中国文人记忆力一定是世界最强,然而看他们写出来的东西没有多少脑子清楚的,说明记得太多未必是好事。笑死了。不过他是严肃的不是开玩笑,有点象福尔摩斯说过,有用的东西记得,没用的东西赶紧忘掉,好留下空间腾挪运转,思考用。当然中文里也有“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说法,我个人觉得问题不在于记忆而是筛选和信任的一种态度。还好,四五百年前发明的科学方法给所有人提供了一套筛选和相信的体系,人人都可以学会——如果我们愿意接受吸收的话。
翻译有些遗憾之处,主要是日文表达形式如果直接硬翻过来就会有种提问/疑惑的口吻,例如,“如果相信了理论A,那记载BCD也就不成立了吧。”之类的句子,在学术文章的语境之下应该用比较正式的口吻写出来,“对照记载BCD,理论A是不可信的。” 日文翻译腔可以跟英文翻译腔一样别扭,既然翻译成中文了就好好说话呗。尤其是对于“景气”这个重要的词,感觉是直接从日文里拿过来的,让我有点膈应,意思显然是某个时期的总体经济状况,不过我一时也想不出合适的替代词。
目前看的上古与春秋战国部分,作者常常跳出来“XX十分可疑”的判断,哈哈,看得我好开心,因为我本来就疑心很久很久了,尧舜禹的事迹,每个末代皇帝都要闹个荒淫糜烂的宠妃,真的假的啊。看到权威历史学家也说可疑真是太爽了。而且各处的说法完全一样,说明都是依赖同一个来源(史记?春秋?),一个来源的历史本来就没法相信。
为什么会把(相对于春秋战国时代)上古的事儿编得绘声绘色呢?宫崎的判断是,这是诸子百家互相别苗头的结果。(也不知为啥)当时的流行观念是古代比较好,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所以找理想社会就得往过去找。孔子大讲(编造?)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等等的贤德事迹,目的是给自己的儒家理论作支撑;墨子觉得这游戏我也会啊,我的理论比你更早呢,夏禹王就是我的理论基础!孟子一看坐不住了,啊呸我还有更早的呢,我的 model 是尧舜,比你夏禹更老更好!大家纷纷比赛着谁更鸟生鱼汤。于是越编越古老,越编越玄乎 ... 然后司马迁写史记时一股脑照收不误,统统当作真实历史写下来。
这时我又想起了 1177BC 里提到的黑暗时代(尤其是缺乏文字记录的情况下)大众纷纷传颂前世的光辉神话,不是英勇神武的 Achilles 就是无比贤明的黄帝尧舜,连老庄也不能免俗。
--------------本人插话的分割线---------------------
为什么这些年我渐渐对于中国上古历史发生了怀疑呢?因为看了一些考古的报道,挖出三星堆!挖出殷墟!挖出良渚!(还有哪些特有名的?)很兴奋地去看,想跟人类基因图谱,尤其是迁徙路线,对应上一些关系。然而失望地发现报道里多是随手跟尧舜禹汤各个王朝画直线的说法,具体证据却是欠奉。例如,殷墟里有关于纣王的文字记载吗?无 ...
咱是对考古学一窍不通,以前唯有对碳14的测量原理略知一二,而已。自从读了 Eric Cline 教授的两本书之后,越发感到考古跟侦探的工作差不多,最好人赃俱获,文字记录与古传物件对应吻合;然而文字本身历史有限,现在能读到的甲骨文不过是2500年前写下的,苏美尔文最早也只是5000年前写的,5000年前的历史嘛 ... 全靠口头文学!我们都知道口头文学有多不可靠,所以在没有(当时的)书面记录时,以实物为准。雅典跟特洛伊打仗,吹得再天花乱坠也没用,拿出城墙和满地青铜箭头来才考虑真实性。所以,在殷墟或马家窑各地挖出来的东西,讲的是什么故事呢?翻来翻去也找不到具体的描述和推理,几乎全是拿着年份直接跟教科书里的夏商周的年代对号入座。挖是挖出来很多东西,测一下年代,有些四千年前,有些三千年前,有些明显是石器时代产物,另一些明显是青铜器,于是被自动贴上了商朝产品,夏朝产品的标签。然而它们有没有上面刻着,为夏朝X王所造?为商朝Y王所铸?我尤其对于甲骨文寄予厚望,这可是实打实的文字记载啊!有没有写明当时是哪个王朝?国王和王后叫什么名字?尤其是,这块地方是否为商朝统治?商朝到底版图多大,如何证实?可惜,这一切都语焉不详。感觉非常不合逻辑,古代文字记录,不管是写在墙上的还是写在纸上的,总是以记录皇家姓名事迹为第一要义,后代有确凿记录都是这个路线。青铜鼎上所著文字,我能找到的最早的是明确写了周王某某的,而更古老的青铜鼎上有没有写商王夏王谁谁铸呢?例如,“后母戊鼎”上面的字儿,很多文章一上来就说这东西是商某王为母亲铸的,然而细查之下,连那个字儿是后还是司都在争议中,怎么知道这是哪个王,哪个母咧?简直细思恐极。各种来源出处的信息碎片拼凑在一起,却不知哪一片是哪里来的,来源是否可靠,有没有 corroboration。这怎么敢信它 ...
那什么样的记录才算正式接受,什么样的说法才能相信呢?举个例子,古埃及的 Ramses 三世法老,就在1177 BC前后坐镇青铜时代最后的荣华,在挖出的纸草书上描述他在宫廷内斗中被刺杀,凶手抓到且被审判,细节历历在目。然而这是不够的,第一,先要鉴定这个纸草书确实是同时代写的,不是几百年后的后人记录的传奇;第二,2011年经过科学家对 Ramses 三世的木乃伊进行深度扫描,证实了颈上足以致命的刀伤,才算是敲定了这件事。在没有敲定之前,只能说,据说是这样的,存疑。
习惯了 Jared Diamond 的啰啰嗦嗦和 Cline 的一大堆 references,让我对宫崎市定的写法也感到不够。当然要考虑到这是一本 macrohistory,跨度极大,不能细细论证每个观点,但仍希望他多提供一些索引,而不是来来去去只引用内藤湖南博士的研究和理论而不提其他原始数据/证据和研究。
-------------------分割线结束------------------------
一旦文字开始被推广,历史记录马上丰富起来。即使著作权问题无法确定——例如《春秋》是否孔子编纂,《老子》是否出现在孔子之后——这些著作本身记录的当时的社会状态和(各种)政治理念,可以互相对照 corroborate each other,这就可信得多了,至少提供了大量原始材料供后人研究推理。(引用一下铜山毛榉里的话,福尔摩斯感觉家庭女教师去应征工作的那家有什么地方不对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唠唠叨叨地说,没有粘土没法做砖头,I need data!)是不是可以由此推理,文字的出现,多半接近春秋时代?估计甲骨文字是在春秋前不久的西周时代才定型的(当然不久也是相对的),这跟青铜器与刻文字的甲骨的年代是一致的——公元前13到11世纪,各方面的证据彼此互证,值得信任。一旦有了系统的文字,思想的传播和交流,也就是普遍意义上的“文化”,便产生了爆炸式增长。同时孔子这种教师职业也红了起来。
作者有一个很好玩的理论,就是为君王服务的“臣”,最早起源是家奴。因为 city states 形成之后,城国(郭)之内的阶级构成主要是贵族/国王(亲戚)versus 平民和庶民,但战俘和劫掠得来的人口属于 slave 阶层,不属于上面两类。而专为国王服务,包括献计献策的那些人,没有明确的身份,跟国王/贵族有依附关系,他们显然是奴(house slaves, not field slaves)。这一点我保持怀疑态度,这至少跟“游说”和“门客”的记录有一定矛盾之处。就算这是指早于游说和门客的“臣”,也需要了解一下证据才能判断宫崎的假设有没有道理。另外他随口说一句古代时干燥地区反而容易发展农业,只要有灌溉技术即可,而低洼地区排水不便并没那么高产。Sounds counterintuitive,需要找找这个理论的来源和研究数据。这本书里经常会冒出来一句两句这样的定论,有些我在别处看过,知道是可靠的,有些没见过,但显然也是有出处的。这时我不禁深深感谢 Diamond 的啰嗦风格了,细细给你算清楚部落游击战一年死多少人,死亡率多少,跟世界大战死亡率比较,等等。
作者经常冒出一句两句的论断还会让我大笑,例如讲到汉朝初期时:
大实话啊!历来中国式的解释全是儒教式的道德论
秦汉两朝
宫崎对于中国的朝代循环的解释,看样子吸收了经济历史学中的主流观点,包括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模型:生产力发展->产量增高->人口增多->资源紧张->社会矛盾尖锐->爆发冲突/战争->死很多人,人口巨减->新朝代建立,重新分配土地,轻徭薄赋休养生息-> 生产力发展 ... 新一轮的循环。按理说,每一代都有人口、土地、农产的数据,司马光(我还想了半天这应该是迁还是光来着)等史官如果搜搜历史资料计算一下,应该能总结归纳出规律来的。也许确实历史上有人总结出来了,但这种理论没有得到推广,实际上得到发扬光大的是儒教式的道德论。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从春秋到 。。。咳咳,他们的职业就是帮助皇上管理庞大帝国里的众多人民和税赋,其中包括教育皇上怎样做决策,宗旨都是维稳,维持皇家传承不倒,与人性本暴和 entropy 自然增加的天然现象不停斗斗斗。当然这种客观规律是没人爱听的。啥?没法预防改朝换代?人类最早的时代,巫师与村长地位相当的时候,巫师的占卜结果,不一定需要讨好村长;但是村长权力高于巫师的时候,占卜结果当然就越来越顺耳了。
在看秦汉历史部分时,一个曾经在脑海里闪过的问题又冒了出来,就是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会爆发革命,什么时候不会爆发革命。这不是本书的主线之一,只能从各类蛛丝马迹里搜寻历史规律,是另一个话题了。
Anyway, 总算搞清楚汉朝的前因后果了。过去也模糊地听过王莽是理想主义者的说法,只是没明白为啥,原来如此,信了圣贤书,想推广美好的政策理论,但却不知怎样下手才有效,于是 ... 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 而且光武帝刘秀也不是啥王室血统,说到底还是枪杆子说话最响,从西汉到东汉,其实是同姓的改朝换代。忽然历史变得很有逻辑了。
The more things change, the more they stay the same. (汗,看本中国史冒出辣末多的英文谚语,是说明人性广泛相同咩?)从西汉开始宫廷斗争的主题就是宦官 versus 朝臣,接下来两千年就是没完没了地上演同一出电视剧,over and over,只要皇权结构没变,内党和外党和皇帝就斗来斗去循环往复(哼,谁说中国历史上没有三权鼎立?)。
作者屡次提到经济问题,例如西汉时期,中原境内有大量黄金,但西汉之后就很少了,说明黄金大量流往西亚导致国内流通性下降,货币短缺,“景气”衰退。可惜这些部分一带而过,没有细节阐述历史证据。例如,西汉时代真的有很多黄金吗?流通到西亚的贸易换过来的是什么产品?注意,南美印加帝国向西班牙葡萄牙流失黄金,只有一部分是通过贸易,而很大一部分是被劫掠的,然而西汉并没有被外族大规模劫掠的记载。I'm sure he based the theory on something but I'd like to see what it is. 自从王莽之后,白银与铜钱成为中原货币,直到近代,这是人所共知的。
汉朝的经济萧条下,出现 currency hoarding 现象,货币被囤积,甚至铜钱锈烂,市面上的流通性急剧下降,加重了经济萧条(“不景气”)的状况,越萧条就越囤钱,形成恶性循环。看到这里我脑后的痒越发强烈,说不出的熟悉。Isn't this a problem of liquidity? Didn't we just hear about it in 2008? Are they fundamentally the same phenomenon? 终于想起来,宫崎近市所描述的跟我所了解的 Keynesian 经济学理论重叠起来了。当然我并没有拜读过经济学理论,连家属硬塞给我的 Paul Krugman 的纽时专栏也懒得看,所知的那点屁事儿都是靠家属转述。例如,为什么北美和欧洲的中央银行拼命印钞票十几年二十年,往社会金融注水,却不见明显通胀和工人工资上涨?仅归结于机器人吗?家属经常引用 Krugman 说,因为贫富悬殊,富人守着越来越多的钱不花出来。所以股市指数狂涨但人民并不觉得富裕。
这就是让我脑内发痒的地方。
西汉末期(后来在东汉末期重复,以后大概也是经常重复),富人囤积铜钱的效果实在有限,据记载,满仓库的铜钱都锈掉。比敛财和守财更可靠的方式是,当当当,土地兼并。(参见伦敦纽约迈阿密温哥华等世界富豪藏钱处的地产价格走向。)称之为大户也好,富人也好,贵族也好豪门也好,反正就是社会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太多钱财没处花掉,同时大多数人口越来越穷,全社会整体消费增长速度慢或减速,加剧市面的不景气,导致经济衰退和萧条。经济萧条让富人更不敢投资发展生产,而是用购买不动产来保证自己的财富。于是...土地兼并。土地兼并的结果是把越来越多的农民扔出来,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打工,而不能拥有自己的土地,或者变成流民,这就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性和农民起义/内战的风险。正是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和无产阶级,为黄巾军、李自成、农民起义、法国大革命等等动乱,提供了足够的柴火,They are the most desperate and ruthless bunch. Have nothing. Have nothing to lose. 难怪要说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因无产而可以亡命。没有干柴,火焰就算燃烧起来也会很快熄灭;没有流动的无产阶级,革命就算爆发了也无法维持下去。
啊啊啊,工业革命拯救了百姓这种不是当农奴就是当流民的命运,统统搜集到工厂流水线上就不必四处流窜闹革命了,社会的稳定也不再靠土地分配来维持。(虽然,不动产仍然是最基本的敛财手段。)财富集中贫富悬殊的路线继续加剧加剧加剧,社会不可能千秋万代稳定不乱。The things modern economy and politics obsessed over --- employment rate, inflation, inequality --- are things human societies have lived through for two thousand years. 由于贫富分化逐渐加剧带来的社会压力,在欧洲以战争和殖民发泄,在中国以换代和土地改革发泄,循环性的宿命。现代社会与古代的差别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巨大,参见二十一世纪美国政治,俄国大亨扶植的傀儡是美国地产商,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读书速度慢找借口的分割线---------------------------
这本书看看停停,速度很慢。跟看 1177 BC 那种好多知识点要出去查维基不太一样,中国史带来的停顿是自身内在的消化。经常看了几句会迷糊起来,又熟悉又陌生,需要在脑子里 reconcile 对于中国历史的原有理解(a mishmash of my education and hearsay)和作者提出的理论,以及对照中国之外的世界史,这个 frame of reference 经常换来换去,把我脑子换晕了。例如农村与城市的形式变化,直到汉末三国期间才从 city states 演变成与现代类似的状况,这就让我感到很错乱。还有作者描述各种不同的人身依附形式,从可以买卖的奴隶到各种半依附的形式,之前完全不了解,只是在“红楼梦”这种古代故事里间接得到的印象,对照起来还真迷幻得很。
作者提到被历史学家误读的“衣食钱”,不是老爷主子发给下人的衣食工资,而是主子把人从小买进家里养成家奴花的衣食钱,所以当这个人被卖给别的主人时(想必也包括把自己赎身出门时)就要付给原主人“衣食钱”。这个词自然而然就让人联想到了“衣食父母”这个词,对不对?瞬间让我产生一系列联想,对于中国文化中的心理结构,尤其是人和人、阶级和阶级之间的感情关系,突然产生新的理解,一时也说不清。总之冲击感很强,不得不把书放下慢慢消化,所以就读得很慢啦。
-------------------借口结束的分割线-----------------------------
魏晋南北朝
宫崎提到曹操实施的严刑峻法,martial law 的严厉措施,是汉末混乱形势下的不得已的政策。这是之前我(这个孤陋寡闻的人)没听说过的。且不说它是否准确,但评价历史人物和他们的政策,必须放在当时的 context 之下来理解,而不是拿自己习惯的(现代)一套思路去套他们,这是很重要的方法论。这一点其实也可以在陈寅恪的历史分析里看到,按照当时当地的情形,推理出决策者的动机,而不是拿着死板的旷世原则和主义来贴标签道德判断。
例如一段我从未听说过历史:曹操当时为了对抗南方的蜀吴,并实现统一中国的大梦,除了施行军田制度(一边备战一边种地,不是不象南泥湾的),还引进了大量的北方外族军队来巩固自己的军事实力,跟现代雇佣军的概念差不多。这些异族军队在华北长期驻扎,后来直接导致魏晋时代的五胡乱华。天啊这也太合逻辑了!为什么正史中几乎不见人提起?曹操被后世文人一致抹黑,跟这件事有关系吗?而且,为什么这件事如此眼熟呢?咳嗽吴三桂咳嗽,咳嗽宋徽宗咳嗽。实际上作者暗示这种民族混乱的军事编制是常态,例如雇佣西域的鲜卑军人去打鲜卑叛军,或者利用南匈奴攻击被匈奴,最方便的代价当然是让他们占领和统治取代的地区,至于后患什么的也来不及考虑了。这样的做法显然是贯穿整个历史的,并不限于魏晋。
读此书时我会经常有被“糊一脸”的惊诧感,不得不放下 Kindle 安抚一下被吓坏的幼小心灵。原来北方/中原跟所谓外族的联系那么紧密,修筑长城把外国人挡在墙外的神话只是极其片面的历史的一小块,而一大部分则是反复的断断续续的,既民间又官方的民族/边境拉锯和混合。当然过去我也猜想过各民族之间一定有“灌来灌去”的现象,那是建立在普遍人类特征上的推理而已,没想到政府本来就经常利用外族人的力量,也不得不放任他们的移民和扎根。再次感叹一下,只有下层百姓才会傻到真信了民粹主义理念,Make XXX Great Again,XXX First,挥舞着旗帜喊口号。实际上皇上和贵族们从来都是 pragmatic 国际主义者,只要对自己有好处就随便用,爱国主义,民族纯洁性,给人民洗脑的工具罢了。Do as I say, not as I do.
这是什么感觉?打个比方,就好象有些人成年之后忽然通过 23andMe 基因测试发现了 half-siblings 存在于世!虽然他们的父母曾经表现得忠贞不渝,道貌岸然,并对婚外恋一直深恶痛绝!现代中国人民被灌输了几代人的理论,中华文化唯我独尊封闭自守,连比较 liberal 学者们都这么说,原来不过是俗套的 fiction,共同编织的理论构架。
南北朝这段历史,看得我颇为痛苦,回忆起初中学历史的各国平行示意图和犬牙交错的年代。就说齐,不是春秋战国的齐,南朝有个齐(宋齐梁陈倒还记得),北朝也有个齐(中文里字那么多,你们选国号不能错开吗?),就一个魏国还一会儿东西一会儿北来着。而且动不动就是军阀杀了当朝皇帝篡位,篡完没几代又被杀掉被篡位 ... 扶额,搞得清楚才怪。
 。
。宫崎顺手讥刺了一下历代中国史官们对于各代王朝的“正闰之分”争论不休,非要定出个正统来,对于好几国/政权同时存在的时代是毫无意义的,但拦不住后代史官们对于“正统”的 obsession。我以及度人,猜想他们会不会也象我这样被搞晕了脑子,老想简化成一正几副的结构,只记录正史,其他可以偷懒忽略 ...?好吧这是我瞎扯的,更加合理的可能是,每一朝代从皇上到大臣,内心都很清楚,看上去坚不可摧犹如神授的皇权,其实分分钟可能裂成碎片,或被大将军篡位,或被宦官篡权。越是明白这一点越要强调正统,天命,不可替代,唯我独尊,the chosen one,历史必然;其他人都是 pretenders, usurpers,闰枝,终将灭亡。只有百姓才会傻到相信这套神话。其实这一套跟一神论 (monotheism) 颇为近似,暗示了社会组织形式的需要,虽然与事实相悖。
当年引入雇佣军的后果就体现出来了。北朝各国的国王大多为外族酋长,而非汉人,北魏皇帝即鲜卑族,迁都到洛阳后,鲜卑贵族阶层全面汉化,改汉姓,用汉字,等等措施,力图与原有的汉人势力融为一体。姓石的,姓苻的,姓宇文的,等等,也不知原语言里姓啥。北魏虽然进驻中原,但本族人数太少,不够巩固长期统治,各部落之间的军队斗来斗去十分动荡。此处很简略,没有细说当时(近三百年)到底哪些民族和部落进行了长期战争。例如,随手搜一下“独孤”之姓,有些说是鲜卑,有些说是匈奴。我回想起那只中国版图变化视频,忍不住再次对于“鲜卑”这个概念产生强烈怀疑,这是同一民族吗?还是本来有很多部落?也许汉人史官也搞勿清楚他们各自的来源和归属,都一股脑地随便贴上一个标签拉倒?
乱了半天终于讲到杨坚统一北方,建立隋朝,再南下灭陈(李后主)统一中国。我擦擦额头的汗,深觉还是统一好,好记!
隋唐五代
看到隋文帝杨坚之父、隋朝之前的西魏皇帝宇文泰(不是汉人)、之后的李渊之父(可能是汉人)诸位都是出身于武川镇的军阀,而武川镇在内蒙古境内,这时我又没忍住好奇心,去搜杨家祖籍到底是不是汉人。一看被惊到了!杨坚本人,小字为那罗延。
宫崎作者描述北方汉族政权被“野蛮部落”推挤,南迁建立南朝(过程跟北朝一样动荡血腥),与当地的原有豪门势力发生各种冲突。这时他沿用了中国史书一贯的定义,assume 南下的北方贵族跟南方的本地人都同是汉族人。然而,我的怀疑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从基因迁徙图来看,很明显中国南方和东南沿海一带的基因来自南亚及太平洋(东南亚)方向,跟中原北方人来源完全不同,实际上是不同的种族群体。当然从春秋战国时代往后,南方不断被北方下来的人群渗透和占领,北方势力每次南下都需要大搞政治,挣扎着与南方土著建立和谐的统治和共处关系,哪怕在血缘上南方人与北方人确非同族。
这下子问题就来了:什么是汉族?
带着这个问题看下去,唐末与五代十国的部分,读得我深感 deja vu 魏晋南北朝,思路十分混乱,理不出一个清晰的头绪。举个例子,书中写道:
在与后唐作战时,(后晋高祖)石敬塘从新近崛起 ... 的契丹那里借来援兵,并将长城内的“燕云十六州”作为成功的谢礼割让给契丹,为后世埋下了长期冲突的种子。
石敬塘这个名字我模糊听说过,燕云十六州倒是耳熟,因为最近才搜过澶渊之盟的事儿嘛,辽宋之间的拉锯战就围绕着这片地,原来是后晋留下的历史遗留问题。这后晋与辽的民族之争真是耳熟之极啊,不是么?不出意料,我又产生了疑心,去查了一下石敬塘条目,果然不是汉族人!实际上五代里就没几个汉族人 ... 吧?灭掉唐朝的人,除了黄巢和朱温(朱全忠),很大一部分是沙陀国军阀(?)——例如李克用(这名字也是模糊印象),别看他姓李,也不是汉族人。在后晋。。。高祖之子初帝时,朝廷中民族主义的国粹论高涨,耻于对契丹执臣下礼,要求实现地位对等的国交,并停止馈赠年例。
书中随口提了一句(象到处埋下的地雷一样动不动就炸我一下),“移居到山西省北部晋阳的沙陀部族酋长李克用”,Wait, what? 这可不是甘肃青海哦,说明唐代期间西北各部落已经移民深入到山西?前面还提到过,安禄山的据点是河北。可是我们不都讨论过吗?安禄山确凿是胡人,不是汉人。
说实话我的地理知识已经全部交还给中学老师了,只好去看看中国地图,确认一下河北与山西的位置。果然,河北就在内蒙古南面嘛!别忘了隋唐主要军阀的来源就是位于内蒙古境内的武川镇。山西也在隔壁。
虽然没有人拉开天窗说亮话,公开地讨论每一次历史上发生民族大融合,到底是怎么个融法的,但读完这几章后,我的脑子里已经浮现出跟《长安十二时辰》完全不同的画面:The entire northern China was overrun by dozens of different tribes and peoples. 就算“汉族”人数仍然是多数,但必须维持自身政权的皇家贵族,却未必是“纯种”汉人。这些异族移民,有些是北方南迁的,有些是西方东迁的,长期驻扎定居,必定与当地土著(汉人?)有持续的通婚和血缘交换——连皇家都是混血,下面的各级军民就更别提了吧?常有说法,称长安为类似于君士坦丁堡的国际大都市,甚至被幻想成“万国来朝”的等级形式。然而教科书并不提及,隋唐时代种族混杂的状况范围有多广,时间有多长。别忘了西北方游牧民族大举渗入中原地区,驻扎军队且广泛定居的现象,至少从魏晋开始就进行了几百年。鲜卑贵族已经修改身份自认汉族了,隋唐两代根本就是胡汉不分,而后面的五代更是 ... 沙陀国据说是突厥人的分部。所以到了宋朝,就算在理论上“统一中华”了,也不等于能够进行种族大清洗,把过去几百年里搬进来的各种胡人和他们的后代骨血统统剔除出去。这时还能分清孰汉孰胡吗?
这样看来,宋朝跟契丹、金、西夏等边境各国的持久拉锯战,忽然变得极其合乎逻辑了。野蛮部落突然南下劫掠抢夺汉人的财富么?没那么简单,他们曾经长期反复进进出出中原地区,与汉人做过街坊邻居,并不是《天龙八部》里描写的完颜阿骨打在长白山打猎,从没见过但是向往南方的富庶。金庸显然历史比我强多了(废话!),设定于北宋的天龙八部里三个男主角,倒有两个是外国人,什么北乔峰南慕容,两个都不是汉人!还挺真实的嘛。不过契丹人和汉人在边境两边互打草谷的片段,以及中原武林对于契丹裔萧峰的敌视,就感觉完全是现代的边境与民族的视角,而并不符合北宋前后的历史状况。
我忍不住想起几个月前在 Smithsonian 的 Natural History Museum 里,参观人类迁徙时间线,听见旁边犹太小哥充满民族自豪感地指着“农业发明地”说:这就是我们以色列!确实地方是没错,然而一万两千年前在此地发明农业的人们,却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阿拉伯人,但也不能说他们跟现代犹太人/阿拉伯人彻底无关。只能说,现在生活在那块地方的人,与当时生活在那里的人,实在算不清楚什么“我们”、“你们”的差别。当年那些人留下了一些基因,又经过一浪一浪又一浪的移民的混合,直到今天,当年的文化是荡然无存了,当时的宗教也肯定不是现在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当年的文字只留存在几片泥板上我们看不懂,只有生物的痕迹还能找到一些。推而广之,现代的XX人(XX=汉族,犹太,突厥,蒙古,雅利安,等等)跟几千一万年前的XX人,是完全不能靠地点来划等号的。所以,生活在2019年的北京的一个汉族人,跟公元四世纪在此地生存的汉族人,又有多少共同点呢?经过多少代移民 DNA 灌来灌去的浪潮冲刷,恐怕现代北京的汉族人,在基因上与五代的沙陀人或者宋代的西夏人更接近吧?
这是一种因为颠倒上下而眩晕的感觉。我从小被动听了不少岳飞传杨家将之类的评书和京剧,黑白分明的界限分成“我们”与“他们”,国家之争。到底谁才是“我们”呢?反而是杨五郎娶了外国公主生下一大堆混血娃,可能更接近历史真相。
这个定义的问题,其实连宫崎市定自己也无法逃脱。他在书中屡次提起,从西北方入侵中原的“异民族”(他称之为“朴素主义”的民族和部落)和他们本来的政治结构,很容易被汉族文化“腐蚀”,变得贪图安逸,奢华挥霍,失去战斗力。然而,这个腐蚀野蛮人的汉族文化又是属于谁的呢?用后代的汉人文化等同于“民族大融合”发生之前的汉人社会,不太合适吧?整个中世纪的华北中原地区(包括黄河区域)受到各族势力的持久入侵和渗透,还有多少汉朝文化与政治的遗产呢?例如,科举是隋朝发明的哦,隋朝与异民族的关系也极其紧密难以切割,谁能精确地定义哪些文化是本地的,哪些是外来的,哪些是移民与本地人混合后的产物?世界上真的有一种持续的、可辨认的“汉人文化”吗?冲进来又留下的“野蛮”异族,只是受众而非始作俑者吗?
确实也有一些文化和政治元素,从汉朝到隋唐到宋朝,穿过了几百又几百年的动荡,被持续保留了。例如,皇权集中制、土地分配斗争、儒家哲学理论、宦官与朝臣的冲突。这些传承持续的元素,与其说是“汉人文化”的强大同化力,不如说是适应地理经济条件的必然结果,即使皇家血统未必是汉人,但胜利者经常(未必每次都)会选择这些政治手段来进行统治。这些手段必然有其作用。就好像,二十世纪里,世界各地有许多国家采用了马克思主义作为统治理论,虽然马克思是德国人,而采用者却各国都有。马克思主义只要好用,其实与种族/民族/国家的身份无关联。儒学官僚专制体系,也差不多,汉人当皇帝也好,满洲人当皇帝也好,这套体系适合统治这里的农业帝国嘛,在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新理论之前,也只好将就着用了。甚至,同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爱国主义,只要在统治上好用,有效,也是全世界的领导人都很爱用的工具。
宋朝
书中提到宋朝得以统一天下,主要原因是之前的周世宗已经将统一事业做了一半,手下大将赵匡胤篡权登基后继续而完成。另一个原因是分裂的众多小国状态无法维持下去:
也许这就是天下分久必合的原理。管理中国这个农业帝国的成本是巨大的,所以才需要科举和庞大的官僚体系,以及对农民的沉重的税和赋。唐朝在富裕的时候还能维持,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就破产分裂了。但是,为什么中原地区可以循环反复地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的皇权,而世界其他地方基本上不行呢?大概得去看看 Guns, Germs, and Steel 里面的农业理论。宫崎市定这本书里提到一些线索,例如,盐的地域性出产,自唐代开始各代朝廷都对盐施加重税并严格管理,令相隔很远的各地之间不得不建立极其紧密的贸易关系。(吴越、闽和南汉诸国)因为领地狭小,维持独立格外艰难,必须在农业以外通过 ... 贸易,或者 ... 特殊产业来增加收入,以供养官僚和军队。各国的努力形成互补,才能勉强保持均衡。
一个帝国如果疆域广大,一统天下,就能建立很大的区域性经济优势,在罗马帝国与汉朝和唐朝(当然也包括现代帝国们)已经证实:有了国家机器来保障贸易交换通畅无阻,令交易成本低廉。而割据分裂的形势下,贸易成本偏高,并且供应链十分脆弱,一环断裂可能带来全面崩溃,这方面可以参见 1177BC。在庞大帝国的治理下,区域性生产可以变得狭窄和专业化,即 specialization,非常依赖贸易维持本地民生。例如加勒比海地区树林被砍掉,只种甘蔗和橡胶,例如哥伦比亚供应全世界的香蕉和可卡因。此类高度分化的经济,带来高效率的生产,但也增加了管理和协调的成本,以及区域的脆弱性。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与经济结构是互为因果的。
忽然意识到,其实上面的观点也是很不准确的。我们提起欧洲总认为他们的常态就是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各国各族,与中华帝国大一统的形态相反,但实际上在历史上也是帝国与小国,统一与分裂状态交错着出现。谁能一口咬定,沙俄不算帝国,奥匈不算帝国,罗马不算帝国呢?我们眼里的本质差别,也许只是时间上的分别罢了。
(离上次更新已经过了一星期,然而我还在宋朝章里陷着。)
我很喜欢这本中国史的原因,除了作者风格颇为 blunt 之外,是他结合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的描述,形成一个 whole picture,就算不能面面俱到,至少能给读者留下相对全面的概念和印象,而不是象传统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那样,局限于政治为主,经济为辅,只描述内部状况而忽略外部环境的死板叙述。例如,宫崎指出北宋政府的主导思想是用钱治国,每年给辽国付钱,换取边境和平,拿钱雇佣军队守卫首都和边境(versus 征兵役),官府除了编制内的官员外,还雇佣平民办事(胥吏),等等。这个金钱治国的风格,显然跟当时贸易繁荣,货币经济发达有直接关系。 In many ways, these approaches are very modern. 但是,开头管用甚至先进的方法,在改变的环境下可能就不再适用,在宋初好用的政策,一百年后就出现弊端。这是一切政治系统的共同规律,从 Greenland Vikings 到复活节岛上的酋长,都不能避免,前面的系统越成功,后面掉转船头改革就越费力。改变是不可避免的,不是从内部改就是从外部改,不是自愿地改就是被迫地改。当然,王安石就是致力于改革的代表。
(拿钱解决一切问题的思路,又何尝限于宋朝朝廷呢?在个人生活里也是非常泛滥的信念。如果世界上的事真的都这么简单就好了,可惜 ... )
这让我又回到一个老问题:理论上我们都知道用马后炮的现代眼光评价很容易搞错,但实际上穿着别人的鞋子走路可真没那么容易呢。Ned Stark 愚不可及,Catelyn 专爱捣乱,崇祯性格恶劣,清末皇帝只想卖国,等等。胖大叔说过,世上没人一早醒来奸笑着自问,今天干点什么祸国殃民的坏事呢?(Although nowadays I am not so sure.)也没有人一早醒来奸笑着自问,今天怎样动摇帝国根基让王朝早点垮掉。当然,他们也许更关心今天怎样才能让自己升官发财荣华富贵,没心思考虑其他人死活,这倒是很常见。很多后人看来是大奸大恶的决定,当时看过去可能是正确或唯一或没啥大不了的。(Again, this is forcing me to consider the humanity of people I hate. 难度高哇。 )
宋朝这段也看得经常搅起复杂的感情,为啥呢?终于出现了大量眼熟的东西,例如文官掌权,官僚体系庞大,压榨劳动人民到极端,战斗力极弱 by design,朝廷文官为了名分斗得你死我活,全不顾兵临城下亡国在即。如此等等。但是,我又脑子发痒了。
一方面,北宋朝廷跟辽国结盟之后两边都开始纵情享乐是真的,宋朝皇帝严防武将势力也是真的。另一方面,中原的军事力量自古以来就受到西方与北方的威胁,真正原因不是政治体系而是战争装备,也就是 ---
马
注意汉朝和唐朝两个武功显著的朝代,都是与西域交易和 access 特别强的时代,也就是能够搞到够多的马匹的时代。就算能搞到够多马匹,还得有够多骑兵,所以自魏晋开始就雇佣大量的异族雇佣军,当然他们带来的隐患大家都看见了。
宋朝富裕,用钱买了一百多年的和平,然而终究维持不了太久,从此之后中原总是打不过北边的异族势力,实际上中原本来就打不过北方或西方的异族。主流历史理论总是用政治制度来解释,用文官高于武官来解释,但如果他们一直都有足够的骑兵和战马,也许政治制度就毫无意义了。
这一点书中并未讨论,但作者提到金国崛起并得以灭掉辽国,一大原因是他们的冶炼铁器(武器)的技术。而蒙古部落的崛起,跟辽国陷落后解禁获得金的铁器有很大关系。Again, 政治也好,文化也好,或者程朱理学鼓吹的个人道德也好,都不及技术的关键作用。
北宋看样子就对于 horse acquisition 兴趣不大,到了南宋那是想搞也搞不到了,也许这才是宋朝反复挨打战败最后被灭的原因吧?元朝面临的问题正是中原与边境各国的长期问题:农业发达的中原,尤其是长江以南地区,必须发展农业,在四周环绕的马背民族眼中,怎么看都是一块不能不吃的肥肉。然而他们进来之后怎样管理巨大的农业帝国呢?最后只有满洲统治者算是 sort of 吃下来了,之前的各种失败倒也不奇怪,但并非是大汉中华的文化吸收力强大。
元朝
作为一个记性很差的人,我只记得元朝统治下把中国地区人民划分为四等,汉人最低,蒙古人自然最高,然而完全不记得另外两类是什么人。所以,看到书中说四类其实是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时,我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汉人!与南人!分成两类!江北的汉人,契丹人,金人,一股脑儿都算作汉人,并且被普遍征入元朝大军,进而打败南宋,tt..tt..统一中国。南人就是南方的汉人(?),被完全看作与北方汉人(?)不同的类别。何谓汉?八百年前的定义显然与今天的定义颇有不同。
这南北之分贯穿整个历史,果然不是我的幻觉。
前阵子我还在想呢,那些在历史书里被划到汉人之外的民族,从党项到鲜卑到契丹到西夏等等,那些人今何在?原来都变成汉人了呀。 Race/ethnicity is a social or political construct. No shit. 主要还是为了统治而服务的,并不是真有什么意义。
如果有什么持久强烈的汉族共同凝聚力,大概就是科举了,这是不论大江南北的汉人都强烈渴盼的。宫崎称元代重开科举但限制汉人数目,实为鼓励蒙人学习前朝政治制度的手段,汉人录取只是陪衬,但“足以令汉族读书人狂喜”,后代汉族史家“认为仁宗是稀有名君,不惜赞誉之词”。
元末部分,作者充分阐述了对于“农民起义”这一名词的异议。古代务农者为绝大多数,换代时各支军队里的士兵,可能在过去或多或少种过地,但因为各种原因失去了农民这个职业,成为流民或帮派。如果还拥有土地,农民或地主(很难区别定义)是不会去参与革命的。所以给这些人定性为农民颇为不妥,我可以理解作者的角度。同时我觉得毛的立场也并非完全错误,虽然领导者可能是小军阀甚至读书人,但没有士兵在下面就没有领导在上面,战争之火总是需要不值钱的很多条命提供燃料来维持,所以社会环境得够坏,制造出大量失业流民才行。
实际上每个朝代末期都是暴动在各地群起,这其中的因果关系需要好好考虑一下。是因为有起义和暴动而导致王朝灭亡呢,还是皇朝衰败才导致各种流民和黑帮揭竿而起。传统的理论是朝廷对国家管理不善,民不聊生,然而我们可不可以换个角度来看,即改朝换代的潜在势力随时存在,并暗流汹涌,一旦皇帝与权力结构 loosen their grip on the masses, 便喷涌不可挡?也许这样的看法在相对稳定的现代社会看来难以理解,但在几百上千年前,民众与官府之间的暴力平衡差异没有现在那么大,官府占有的武器技术没有那么高明,王朝的崩溃的难度也就不象今天那样高了。
明朝
(终于只剩两个朝代了!欢呼!)
作者顺口提了一句,朱元璋统一登基,是中国历史上唯二由南方(长江流域)北伐成功的例子,另一个是蒋介石。但蒋介石是现代实例,在战争技术上已面目全非,所以可以安全地说,历史上自南往北的统一行动只有很晚很晚的朱元璋一个案例,其他都是北人南下的占领和迁徙。
这让我强烈地联想到印度的各部落流动历史。印度没有过强烈而长期的文化统一政策与宣传,所以他们的各族群混杂历史比较清晰,也是有过一浪又一浪的北人南移,不断征服和占领南方原住民的大趋势。
即使是这个唯一的南皇北征的例子,明朝很快又内部重演了一下北方以军事技术优势压倒南方的大形势,即燕王朱棣打败建文帝,篡夺皇位后迁都北京的事件。宫崎指出朱棣的优势来自收编的前朝蒙古骑兵,再次印证了马的重要性。
明朝与北方异族的边境冲突时之前一千多年的历史重演,I seriously believe Chinese history should be redefined primarily by this endless conflict. 但这时明朝开始采用大炮作为武器对抗骑兵,只是技术尚未成熟而没能占上风。
换言之,从汉朝开始,南方的汉人(?)与北方部落相比,就一直处于技术落后的地位。这个技术不是指农耕或商业,而是纯指战争的技术,即马与骑兵。所以种族迁徙持续自北向南流动了两千年。
即使在书里,明朝这章也很短,因为作者认为明清两朝是宋元的重复/镜像,加上一些小小进步,但没有飞跃或质变。
清朝
用战争武器的角度来看中国史,能部分解释满洲清朝的成功。可以说他们是自唐代以来最成功的北方统治南方的实例,既有强大的骑兵储备而不需要“借兵”于北方游牧民族(他们自己就是),又有热爱南方文化和政治体系的意愿。不象蒙古元朝,女真族人一直都对南方汉人的帝国有兴趣,也许通过辽国的繁荣与衰败的例子发展出一个统一中国的计划。明末皇帝与将领很想跟关外清军建立类似宋辽条约的关系,但人家已经看到了元朝的先例,知道一统中原是可能的,就再也不肯安于共存的形式了。
另一个感想是国家与民族的标签也许会湮灭于历史的浪涛里,但人民与集体记忆却未必。金国是灭亡了,但三百年并不是短期,而他们能够卷土重来,提醒我们标签的出现与消失并不能解释现实的变迁。类似的,标签的长存也只是标签而已。我常常想起 Cotzee 讥讽 TS Elliot(精神英国人)非要把现代英国文学说成是罗马诗人 Virgil 的一代单传,这跟现代中国政府非要把自己说成是秦始皇嫡传有什么两样呢?
宫崎大叔在宋朝章就早摆出汉族对女真族的文化影响,跳过三百多年的元明两朝,终于在清朝里全面爆发,才导致清朝皇帝热衷学习和 adapt to 对汉人的政治统治。例如从顺治开始每个清帝都通晓汉文,读写没问题,康熙和乾隆还花大笔银子编纂汉文书籍和索引,完全是一副吃透汉人历史与文化的架势,这是其他朝代,包括汉人的朝代都没有过的政策。所以,现代的“汉族文化”其实跟清代满洲皇帝的立场与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许彼此渗透难分你我。
可以比较安全地说,宋朝和明朝的汉人皇帝颇为接近现代意义上的汉族人,而之前的统治者就很难讲了。
在乾隆之前,还有哪个皇帝(民族不算)如此疯狂地收集南方汉人书籍的呢?没有了吧?宫崎指出这个现象的潜在动机是巩固统治。
作者随笔提及英国进口鸦片初期,毒品贩卖帮会的组织形式颇象之前私盐帮派,第一个威胁到的就是官方政治体系,第二才是威胁到人民健康和生产力。很有趣的观察,而且跟美国禁酒期间黑帮借贩卖私酒而大盛的现象如出一辙。如四库全书的编纂,隐藏的深意是检查全国图书,欲肃清不慎留下的攘夷记载。。。这场搜查禁书事业进行得非常彻底。
民国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得以统治全国的关键一步是北伐,这是之前孙中山北伐失败后的成功,也是历史上第二次南方战胜北方的实例。原因很明显,现代武器取代了骑兵重要性后,南北差距已经消失,马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很有趣,宫崎评论共产党的胜利,把它归结于不仅日本而且美国。日本的侵华战争的作用大家都知道了,但,但美国呢?他认为国民党军队的虚弱,原因是“被美国拜金主义毒害的干部的腐败”。
本书的后续中,作者很霸气地解释了为什么很少引用原文文献,原来这本历史概述是全凭自己的记忆写出来的,不记得的段落就略去不写,因为不记得就说明不够重要!
可惜我不懂经济学,对宫崎多次讨论的景气与货币经济看得一头雾水,笼统地理解,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即景气)可以从货币流动性间接推断,其中一个原因是铜钱上印了字儿,因此知道哪个皇帝当权期间发行了多少铜币,从而得到客观的经济数据。简单粗暴地说,经济状况繁荣 and/or 贸易发达,则朝廷会发行更多的钱币,后世也会收集到更多的“开元通宝”铜币。他还提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政府发行的(含铜量高?)良币很容易在民间被融化重铸为(含铜量低?)劣币,而铜钱的背后靠相对稀少的银子支持(西汉时中原是否黄金满地的问题暂且搁置,银子的确是历史一贯的硬通货),劣币的铸造无法彻底控制(管理成本之一?),所以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而 currency hoarding 的原因主要是社会的生产力下降或者贸易受滞,但这两样的原因就很多了,很可能是外界环境变化,例如中西亚的丝绸之路因战乱动荡而切断,也可能是内部衰退,例如国内昏君 and/or 官僚腐败,总之是个 complex system,包含了很多互相影响的因素和无法剔除的动态关联。当宏观形势一路下滑时,就算拼命发行货币也无法刺激经济回到繁荣的上升期;而时运好时连风都是东边吹来的,西边有伊斯兰教统一各民族带来的稳定安全的商业通道。这一切也许都跟政治制度关系不大,文化更是影响微小。
这本中国史概述有很多优秀亮点和出人意料的 insights (例如他说到明清朝代时中国与欧美的技术差别并不是很大,唤醒了我脑子里存在很久但模糊不成形的某种感觉),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主题可能是两条:一,不要被意识形态和理论主义之类的说法迷惑了,抓住事实证据,透过现象(宣传)看本质更重要;二,历史是有规律的,不仅中国历史上看得出明显的循环反复的 patterns,而且跟世界历史对比也能看出清晰的类似 patterns,东西方差别才没那么大呢(换言之,you are not special, we are not special, nobody is special.)。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