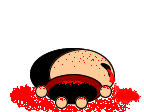[原创]阿得的故事
[原创]阿得的故事
当我在X公司做时,阿得是第三个被雇佣的秘书,前两个在一年半内因为不同的原因而迅速走掉了。阿得看上去五十来岁,黑人,一张口就是粗哑的烟枪嗓门,哇啦哇啦的。眼睛下两只大大的眼袋,摺子不少。头发开始变稀,体型象个锥子,两头细中间圆,裤腰划出一团圆鼓鼓的肚子。每日见她大大咧咧地进了公司,坐下先把网球鞋脱下来,从最下一格抽屉里取出一双旧皮鞋套上。有日聊起,她说她没有车,每日坐公车和地铁上班,要走不少路。我问道冬天下雪怎么办,她耸耸肩:多穿两件呗,再带把伞。"我不开车已经许多年了,坐公共交通多省心。"她说。
渐渐地听说了她的背景。她原来已经年近六十了,但是精力旺盛,做事速度很快,一个人住在Olney,有三个成年子女,都在附近。"他们要我去跟他们住,"她说,"我才不干。我就喜欢自由自在的,懒得再搅到他们的生活和纠纷里面去。我一个人把他们拉扯大,任务完成,别的全靠他们自己负责了。"她做事十分快手,为人爽朗,话多,不几日便跟公司里楼上楼下的各色人等都搞熟了。中午去买饭时,我常见她在大门口抽烟。
一日在公司午餐室吃饭,见阿得坐在一旁边吃边看书。我是见人手里有书就非得看一眼封面不可的,凑过去见她读的是Katherine Graham的自传。我问Katherine Graham是谁,她答是华盛顿邮报的老板,里面有许多本地的历史,上流社会的描述,以及女人在一个男人统治的环境里办报纸的当老板的艰难等等。阿得侃侃而谈,我一旁摸出心里的惊讶。为什么惊讶呢?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假设这个当秘书的老女人文化程度不高,瞧不起人。从此我跟阿得经常聊天,坦白地说是我少见多怪和好奇,过去眼睛长在额角,只认得贴了标签拿了证书的读书人。阿得跟我侃侃而谈,倒是我自己还有几分顾忌,虚荣心作怪,怕同事问我为什么跟秘书有这么多话可讲。
某日阿得一个礼拜没来上班,从头儿那里听说的只是她出了点事故。等她来上班了,大家才吓一跳,脸上青肿,一边额头还盖着一大块沙布,好象被人痛打过一顿。原来她在家做饭时忽然头晕,厨房地面大概溅了油,脚下一滑面朝下栽倒在地,额头裂了个大口子,血流满面。她并无惊慌失措,但是腿脚无力,喘了半天后才爬到客厅打电话给医院,缝了好几针。同时查出来是贫血造成的头晕脚软,而贫血是胃里的旧溃疡复发,也不痛,静悄悄地已经出血很久了,医生一查她的红细胞立刻输了一袋血。她进了医院后才告诉子女。她漫不在乎地说:"瞧,我不是自个儿打理周全了吗?"
在谈话中,我慢慢听说了阿得的一些历史。她母亲生她的时候年纪还小,于是送给亲戚养大,她在养母家长大,中学都没毕业就辍学了--因为她自己也是十六岁就怀了孕。"我急不可耐地搬了出来,找工作养活自己和孩子。我从小就跟养母一家合不来,搬出来才松口气,再怎么艰苦也是值得的。"养母一家并没有虐待她,只是她的性格倔强,生来躁动,不甘现状。"他们讨厌我,觉得我瞧不起他们,说这孩子怎么老以为自己比别人强,不安分。其实倒没说错,我是认为自己比他们强,我看不惯他们软塌塌地做人,怕这怕那。我从很小就明白我跟他们不一样,没有什么是我不敢想不敢做的事。"一个骄傲的小孩子,拒不认命,趴在下面安分守己,让她的养母很头痛。但是"他们是不管有多少烦恼和争吵都不肯开诚布公地讨论的那种家庭,大家只会搞passive aggressive的手段,最怕跟自己的亲人摊开来说实话,憋死人。"例如,她回忆道,十几岁时好奇心重而去读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这本大黄书,结果被养母趁她不在家时在她房间里翻到,阿得回家时只见床上有一堆撕得小小地整整齐齐的碎纸--养母把好厚的书撕碎堆在那里以示惩罚,却跟她一句话也没有提起,假装啥事也没发生过。她告诉我这件往事时,我骇笑了半天,说奇也不能算奇了,我自己和同龄这一代,谁不曾十几岁偷偷地看禁书,又有几个家长跟儿女平静地不害怕地摊开讨论人生?
十六岁辍学搬出来后,阿得一边工作一边养活女儿,她和孩子她爸的关系,并不是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关系。他也是个小男孩而已,没有她一半的坚强和勇气,只是千百个软弱男人之一罢了,尽量出点力,有时贴补点家用, 但终究是靠不住的。他们在一起好几年,后来又生了两个儿子,抚养三个子女的重任都是阿得一肩挑起。二十几岁时,有一天阿得说这样下去不行,我这辈子不能就困在生孩子养孩子上面。于是她跟男友分了手,单身母亲出去闯世界。她在一家nonprofit的公司从秘书做起,因为有能力而得到老板的器重,升到管理阶层。这是一家咨询社,专门帮助少数族裔的承包商争取政府工程和合同。老板是个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的人,而老板的合作伙伴却是个善良的中年单身汉, 日久生情,他爱上了她。
阿得说起老A的时候总是称他为"我的老友"或者就是"老A"。有婚之实无婚之名的长期关系,在称谓上并无定论,现在叫life partner的也多起来了,但是七八十年代,她习惯了老友的称呼。我问:那么,老A是不是the love of your life?她沉吟片刻说,应该是吧?我的孩子都把他当爸爸看待,他也把他们当自己的儿女对待。我又问:你们在一起二十来年,为什么不肯定关系,结婚算了?她不愿多说,只说这种事很难解释。老A也向她求过婚,她也考虑过,可是。。。或许她对孩子们的爸还有旧情,或许天性不羁不愿被正式地拴住,或许她一开头并不特别爱他,但是接受了他的感情和金钱资助, 或许另有隐情--男女私情这种事怎能说得清?名份的事就搁置起来,夫妻一样的日子还是那么过。老A事业成功,给她钱贴补家用时,她也并不拒绝。其实,如果跟他结婚,岂不是可以更加名正言顺地吃定他?一张稳定可靠的长期饭票,对于一个独力拉扯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是什么样的诱惑?但她始终没有接受。儿女长大独立后,他们仍然这么含糊地在一起,她也并没有要他养。
后来,老A查出癌症晚期,他身边只有她一个人陪着他照顾他,送他上路。那一段日子捱的很艰苦,她比他更难,"他去世之后很久我一直非常低落。"她告诉我。她并没从他那里得到太多物质的好处,虽然他给她的孩子们留了一笔教育费。她住的房子是自己的钱买的,她在Netscape干了几年Office Manager,"Enron,Worldcom那些做假帐的事太普遍了,我在Netscape--那时已经卖给AOL--干活的时候看见太多乱搞的事了。他们把我裁员时,真让我松口气。"被裁的时候泡沫尚未彻底破裂,阿得拿了一笔可观的安置费,付了头款后,剩下的拿了去巴贝都斯度假。后来,她告诉我,在那里跟一个比她年轻八岁的男人还有过一场艳遇,她差点就留下不回来了。
本来我与阿得也只是淡交,她有二类糖尿病早期,有时跟我打听有关吃药的事宜,为了健康把爱吃的炸鸡也戒了不吃。冬天她得了支气管炎,咳嗽很久。我劝她戒烟,她下了决心把家里和办公室抽屉里的烟都扔了并且表示不再买烟,如此坚持了一个多月。忽然有一天我在楼下又见她吞云吐雾,笑问怎么忍不住破了戒。她没说什么,过后跑到我的办公室里说想聊聊,然后告诉我她的小儿子刚刚查出了肝癌晚期,已经扩散,她心情很差,所以又把烟给点了起来。
后来我在X公司只呆了几个月便另某他就了,在这最后的几个月里,有那么些个下午,阿得坐在我的办公室里的桌对面,眼光落在我背后的窗外丑陋的办公楼,说啊说啊说的,我只需听着,点点头。
"安东尼脾气象我,"她总是说。"我们俩最了解对方的心思。"
阿得自己高中辍学,她的三个儿女却都是大学毕业,其中也有拿过硕士的, 都是白领工人,中产阶级。她女儿上小学时老师抱怨说她孩子上课不听讲,她问女儿才发现讲课进度奇慢,女儿早会了听腻了;回去找老师,答曰我们只照顾后进生不照顾快进生,孩子聪明也不能开小灶。阿得二话没说就把女儿转到中产阶级住宅区的学校,虽然每日要坐一个钟头的校车,虽然班上都是白人孩子。她对三个儿女说:如果有人跟你说你不能干这个那个,不要理睬,世上没有什么是不能的,不用怕,没有什么可怕的,都是纸老虎。
我好奇:你的胆儿这么大,都是从哪儿学来的呢?她说我也不知道,从小养母家里左邻右舍都骂她心高气傲,不知道安分守己,她小小年纪就不信邪不买帐,不需人教。没有榜样,她简直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反叛。生于民权运动之前的黑人,又是女的,在这样的社会里每时每刻明里暗里到处都是腐蚀人灵魂的瘴气,在你耳边小声嘀咕:"你生来就比别人笨,比别人弱,比别人差,别痴心妄想了,好东西你不配得到。"大学者拿出科学研究"证明"黑人天生智商低于别人,事业有成的黑人无一不被假设是靠着affirmative action才爬上去的。
阿得的小儿子安东尼发现肝癌时已经是晚期扩散,对她打击很大。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案,开始按照医生的推荐去参加尚未批准的新药临床试验clinical trials,象无数癌症患者一样期待着能撞上研制中的特效药。儿子经受化疗十分辛苦,吃什么吐什么,而且躺在床上虚弱得不能动弹。阿得搬过去照顾他衣食起居,如此颠簸了一些日子,她的眼袋越来越大,越来越松弛,烟也抽得更凶。
终于有一天,我问起她家里怎么样,她说安东尼决定不治了,只接受辅助治疗帮他尽量维持正常的生活功能。
我心里一沉,问:"真的吗?"
她说:"他说他宁可站着死也不愿意躺着半死不活动弹不得地拖下去。他打算把剩下的时间都花在跟亲朋好友和一对儿女(他离了婚)好好地相处上,享受生活一把。"
我默然。有勇气做出这样决定的病人并不多见,人总有不灭的希望期待奇迹发生,有时病人家属比本人更加拒绝面对现实,病人已经昏迷不醒而家属还在要求医生尽一切努力抢救。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很多时候消极地辅助治疗反而比积极地下虎狼之药强多了,而治病的"良药"不小心倒会成为加速病人死亡的原因之一,但是谁肯放弃希望,就是医生也经常不肯认输。
我说:"你一定很难过,看着自己的孩子,帮不到他。。。"她几乎恶狠狠地回答:"他一直是个成熟有智慧的孩子,他做的决定我都无条件支持。"他要求最后的日子无论多短,每一日充实度过, 没有遗憾,而不是被困在床上痛苦地捱过去。他的愿望实现了,安东尼在那年秋天安静的去世,被至亲好友围绕,没有太多痛苦。此后阿得有一段很低沉的日子,但是她拒不搬去跟儿女同住。她说自己一辈子依靠自己习惯了,儿女要照顾她,结果只能添乱让她心烦。但是她并不固执,我提议的support group,看心理咨询,她都去了。过了冬,我那时已经换了工作搬到远处,来年跟她通电话时,她说心情已经好多了,又开始戒烟的浩大工程。那一年里发生了许多事,她的大女儿再婚嫁得很好,安东尼自己的女儿也结婚生了孩子,他们一大家子进进出出,离离合合,生老病死。阿得已经有好几个重孙了,她说:我没工夫去理睬他们下一代的事,他们自己去折腾自己的人生吧,我的任务已经完成。
今年我回到本地,约了阿得见面聊天。此时天气已经开始转冷,她见了我时笑笑说:"上礼拜是安东尼去世两周年。"她还象过去一样哇啦哇啦地话多,嘎嘎大笑。宣布计划08年退休,拿了退休金,Medicare,社会保险金,再把房子抵押成reverse mortgage,"我都算好了,钱够用,再无挂心事,我去巴贝朵斯晒晒太阳,在附近做做义工,在附近社区大学选堂课上上。。。"我笑道:"别忘了我老是催你写的回忆录。"跟我解释了半天她是怎么算计各项开支收入之后替自己计划好后路的--"如果一切按照计划实现,我不需要儿女贴补,一切安排地妥妥帖帖直到老死。"我看着她的笑容,叹口气,问道:"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受过高等教育会有怎样的成就。"她想了一想说:"不知道,但是我对这辈子做的所有决定都不后悔。"
"我那时候怀了玛丽亚,一心只盼着逃离那个充满怨恨的家,出来工作养活自己孩子,是我唯一的选择。"我听了脸上不由得红一红--还是根深蒂固的唯有读书高的标准,没了文凭学历,头衔标签,就不知东南西北了。我喜欢听阿得聊天,就是因为她生存在我的世界之外,我在别人铺好的公路上目不斜视地左转右转,从不偏离划好的白线,她在没有路的旷野里赤手空拳独自一人横冲直撞。
她最不耐烦听人说"我不懂","我不会","我不知道"。她告诉我,某同事跟她抱怨说老公在家理财,她担心退休后钱不够用却又无法可想,只有唉声叹气,又怕又担心。阿得把自己收集的各种资料,年金啦,社会保险规定啦,reverse mortgage啦拿来给她看,她瞟了一眼就推开不看说"我不懂,太难了。"阿得厌烦地跟我说:"这种人到处都是,动不动就说我不能。有手有脚,不聋不瞎,肩膀上的脑袋难道是用来摆设的吗?干吗不自己去学?"阿得的胃口很大,对各种事物都有种饥饿的好奇心,她的知识和智慧不是靠书本课堂里教的,而是自己找来自己用,所以没有多余的废话和牛屎,每一样都经过人生的检验。
上次见面,我问阿得作为战后一代在本地长大是怎样的情形和变迁。她说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话,例如,华盛顿地方的黑人跟南方和中西部不同,"我们没有自卑感。"虽然也有种族主义和隔离政策,本地的黑人比较自信,教育程度和经济地位也比较高,很早就有很多专业人士,艺术和音乐成就,见了白人社会不害怕不退缩,跟美国其他地方不同。又例如,她说民权运动后的混合政策(integration)间接地破坏了黑人社区的繁荣和稳定,因为黑人一旦能够在比较富裕的郊区买房定居,比较中产阶级的家庭就纷纷搬出城里传统的黑人社区,留下的全是贫穷的没有出路的阶层,结果恶性循环,城里本来兴旺繁荣的黑人住宅区和还算好的学校都迅速衰落下去。"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在U街附近有很多剧院和爵士音乐厅。我经常带着女儿去看话剧和歌剧。现在那里天黑了都没人敢出门。"
分别时我说:别忘了,有空写写回忆录,不把你的经历见闻写下来太浪费了。她笑道:等我退了休一定写。
后记:上周忽然收到阿得的一封电邮,告知她的诸位好友相识,不久前她因为贫血去医院看病,结果查出肺癌病灶,所幸是Stage 1,没有转移的迹象,近日便要开刀切除一部分肺。我赶紧打电话给她,家里没人接,打到公司,电话里的声音跟往常一样中气十足。
我惊道:你怎么还在上班?她笑着反问:不上班干什么?我发现肺癌已经快一个月了,等到手术日期定下才宣布的。
我说:你现在心情如何,有人陪吗?她说才不要,虽然儿女都劝她搬过去被照顾,她还是照常独来独往,"家里还有大把琐事要料理呢。"
我叹气:你真勇敢,换了我是你的话早就躲在床底发抖,拖着别人的手一刻也不敢放开。她说她不怕,她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恐惧。
我拿着话筒,不知道说什么好。什么样的安慰话俗套话,在这个身经百战的女人面前都苍白无力。两年前我或许会躲在医学技术说法后面,假装镇定自信地说些"一期肺癌应该能治好"的废话,现在我略微少了一点幼稚,而且她肯定把治疗方案,预期prognosis,五年生存机率等等都打听地一清二楚。
"你遗嘱写过了吧?"我问道。我自己想着写遗嘱好几年了都还没动手。
"早写了,还有medical directive, durable power of attorney,早已搞定。"
"可别再抽烟了。"我无力地说。
"我已经一个月没碰烟了。"她愉快地答道。"我下个礼拜五在XX医院开刀,你来看我。"口气就象在说"我要开派对,你来。"
我说好,我一定来。
渐渐地听说了她的背景。她原来已经年近六十了,但是精力旺盛,做事速度很快,一个人住在Olney,有三个成年子女,都在附近。"他们要我去跟他们住,"她说,"我才不干。我就喜欢自由自在的,懒得再搅到他们的生活和纠纷里面去。我一个人把他们拉扯大,任务完成,别的全靠他们自己负责了。"她做事十分快手,为人爽朗,话多,不几日便跟公司里楼上楼下的各色人等都搞熟了。中午去买饭时,我常见她在大门口抽烟。
一日在公司午餐室吃饭,见阿得坐在一旁边吃边看书。我是见人手里有书就非得看一眼封面不可的,凑过去见她读的是Katherine Graham的自传。我问Katherine Graham是谁,她答是华盛顿邮报的老板,里面有许多本地的历史,上流社会的描述,以及女人在一个男人统治的环境里办报纸的当老板的艰难等等。阿得侃侃而谈,我一旁摸出心里的惊讶。为什么惊讶呢?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假设这个当秘书的老女人文化程度不高,瞧不起人。从此我跟阿得经常聊天,坦白地说是我少见多怪和好奇,过去眼睛长在额角,只认得贴了标签拿了证书的读书人。阿得跟我侃侃而谈,倒是我自己还有几分顾忌,虚荣心作怪,怕同事问我为什么跟秘书有这么多话可讲。
某日阿得一个礼拜没来上班,从头儿那里听说的只是她出了点事故。等她来上班了,大家才吓一跳,脸上青肿,一边额头还盖着一大块沙布,好象被人痛打过一顿。原来她在家做饭时忽然头晕,厨房地面大概溅了油,脚下一滑面朝下栽倒在地,额头裂了个大口子,血流满面。她并无惊慌失措,但是腿脚无力,喘了半天后才爬到客厅打电话给医院,缝了好几针。同时查出来是贫血造成的头晕脚软,而贫血是胃里的旧溃疡复发,也不痛,静悄悄地已经出血很久了,医生一查她的红细胞立刻输了一袋血。她进了医院后才告诉子女。她漫不在乎地说:"瞧,我不是自个儿打理周全了吗?"
在谈话中,我慢慢听说了阿得的一些历史。她母亲生她的时候年纪还小,于是送给亲戚养大,她在养母家长大,中学都没毕业就辍学了--因为她自己也是十六岁就怀了孕。"我急不可耐地搬了出来,找工作养活自己和孩子。我从小就跟养母一家合不来,搬出来才松口气,再怎么艰苦也是值得的。"养母一家并没有虐待她,只是她的性格倔强,生来躁动,不甘现状。"他们讨厌我,觉得我瞧不起他们,说这孩子怎么老以为自己比别人强,不安分。其实倒没说错,我是认为自己比他们强,我看不惯他们软塌塌地做人,怕这怕那。我从很小就明白我跟他们不一样,没有什么是我不敢想不敢做的事。"一个骄傲的小孩子,拒不认命,趴在下面安分守己,让她的养母很头痛。但是"他们是不管有多少烦恼和争吵都不肯开诚布公地讨论的那种家庭,大家只会搞passive aggressive的手段,最怕跟自己的亲人摊开来说实话,憋死人。"例如,她回忆道,十几岁时好奇心重而去读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这本大黄书,结果被养母趁她不在家时在她房间里翻到,阿得回家时只见床上有一堆撕得小小地整整齐齐的碎纸--养母把好厚的书撕碎堆在那里以示惩罚,却跟她一句话也没有提起,假装啥事也没发生过。她告诉我这件往事时,我骇笑了半天,说奇也不能算奇了,我自己和同龄这一代,谁不曾十几岁偷偷地看禁书,又有几个家长跟儿女平静地不害怕地摊开讨论人生?
十六岁辍学搬出来后,阿得一边工作一边养活女儿,她和孩子她爸的关系,并不是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关系。他也是个小男孩而已,没有她一半的坚强和勇气,只是千百个软弱男人之一罢了,尽量出点力,有时贴补点家用, 但终究是靠不住的。他们在一起好几年,后来又生了两个儿子,抚养三个子女的重任都是阿得一肩挑起。二十几岁时,有一天阿得说这样下去不行,我这辈子不能就困在生孩子养孩子上面。于是她跟男友分了手,单身母亲出去闯世界。她在一家nonprofit的公司从秘书做起,因为有能力而得到老板的器重,升到管理阶层。这是一家咨询社,专门帮助少数族裔的承包商争取政府工程和合同。老板是个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的人,而老板的合作伙伴却是个善良的中年单身汉, 日久生情,他爱上了她。
阿得说起老A的时候总是称他为"我的老友"或者就是"老A"。有婚之实无婚之名的长期关系,在称谓上并无定论,现在叫life partner的也多起来了,但是七八十年代,她习惯了老友的称呼。我问:那么,老A是不是the love of your life?她沉吟片刻说,应该是吧?我的孩子都把他当爸爸看待,他也把他们当自己的儿女对待。我又问:你们在一起二十来年,为什么不肯定关系,结婚算了?她不愿多说,只说这种事很难解释。老A也向她求过婚,她也考虑过,可是。。。或许她对孩子们的爸还有旧情,或许天性不羁不愿被正式地拴住,或许她一开头并不特别爱他,但是接受了他的感情和金钱资助, 或许另有隐情--男女私情这种事怎能说得清?名份的事就搁置起来,夫妻一样的日子还是那么过。老A事业成功,给她钱贴补家用时,她也并不拒绝。其实,如果跟他结婚,岂不是可以更加名正言顺地吃定他?一张稳定可靠的长期饭票,对于一个独力拉扯三个孩子的单身母亲,是什么样的诱惑?但她始终没有接受。儿女长大独立后,他们仍然这么含糊地在一起,她也并没有要他养。
后来,老A查出癌症晚期,他身边只有她一个人陪着他照顾他,送他上路。那一段日子捱的很艰苦,她比他更难,"他去世之后很久我一直非常低落。"她告诉我。她并没从他那里得到太多物质的好处,虽然他给她的孩子们留了一笔教育费。她住的房子是自己的钱买的,她在Netscape干了几年Office Manager,"Enron,Worldcom那些做假帐的事太普遍了,我在Netscape--那时已经卖给AOL--干活的时候看见太多乱搞的事了。他们把我裁员时,真让我松口气。"被裁的时候泡沫尚未彻底破裂,阿得拿了一笔可观的安置费,付了头款后,剩下的拿了去巴贝都斯度假。后来,她告诉我,在那里跟一个比她年轻八岁的男人还有过一场艳遇,她差点就留下不回来了。
本来我与阿得也只是淡交,她有二类糖尿病早期,有时跟我打听有关吃药的事宜,为了健康把爱吃的炸鸡也戒了不吃。冬天她得了支气管炎,咳嗽很久。我劝她戒烟,她下了决心把家里和办公室抽屉里的烟都扔了并且表示不再买烟,如此坚持了一个多月。忽然有一天我在楼下又见她吞云吐雾,笑问怎么忍不住破了戒。她没说什么,过后跑到我的办公室里说想聊聊,然后告诉我她的小儿子刚刚查出了肝癌晚期,已经扩散,她心情很差,所以又把烟给点了起来。
后来我在X公司只呆了几个月便另某他就了,在这最后的几个月里,有那么些个下午,阿得坐在我的办公室里的桌对面,眼光落在我背后的窗外丑陋的办公楼,说啊说啊说的,我只需听着,点点头。
"安东尼脾气象我,"她总是说。"我们俩最了解对方的心思。"
阿得自己高中辍学,她的三个儿女却都是大学毕业,其中也有拿过硕士的, 都是白领工人,中产阶级。她女儿上小学时老师抱怨说她孩子上课不听讲,她问女儿才发现讲课进度奇慢,女儿早会了听腻了;回去找老师,答曰我们只照顾后进生不照顾快进生,孩子聪明也不能开小灶。阿得二话没说就把女儿转到中产阶级住宅区的学校,虽然每日要坐一个钟头的校车,虽然班上都是白人孩子。她对三个儿女说:如果有人跟你说你不能干这个那个,不要理睬,世上没有什么是不能的,不用怕,没有什么可怕的,都是纸老虎。
我好奇:你的胆儿这么大,都是从哪儿学来的呢?她说我也不知道,从小养母家里左邻右舍都骂她心高气傲,不知道安分守己,她小小年纪就不信邪不买帐,不需人教。没有榜样,她简直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反叛。生于民权运动之前的黑人,又是女的,在这样的社会里每时每刻明里暗里到处都是腐蚀人灵魂的瘴气,在你耳边小声嘀咕:"你生来就比别人笨,比别人弱,比别人差,别痴心妄想了,好东西你不配得到。"大学者拿出科学研究"证明"黑人天生智商低于别人,事业有成的黑人无一不被假设是靠着affirmative action才爬上去的。
阿得的小儿子安东尼发现肝癌时已经是晚期扩散,对她打击很大。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案,开始按照医生的推荐去参加尚未批准的新药临床试验clinical trials,象无数癌症患者一样期待着能撞上研制中的特效药。儿子经受化疗十分辛苦,吃什么吐什么,而且躺在床上虚弱得不能动弹。阿得搬过去照顾他衣食起居,如此颠簸了一些日子,她的眼袋越来越大,越来越松弛,烟也抽得更凶。
终于有一天,我问起她家里怎么样,她说安东尼决定不治了,只接受辅助治疗帮他尽量维持正常的生活功能。
我心里一沉,问:"真的吗?"
她说:"他说他宁可站着死也不愿意躺着半死不活动弹不得地拖下去。他打算把剩下的时间都花在跟亲朋好友和一对儿女(他离了婚)好好地相处上,享受生活一把。"
我默然。有勇气做出这样决定的病人并不多见,人总有不灭的希望期待奇迹发生,有时病人家属比本人更加拒绝面对现实,病人已经昏迷不醒而家属还在要求医生尽一切努力抢救。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很多时候消极地辅助治疗反而比积极地下虎狼之药强多了,而治病的"良药"不小心倒会成为加速病人死亡的原因之一,但是谁肯放弃希望,就是医生也经常不肯认输。
我说:"你一定很难过,看着自己的孩子,帮不到他。。。"她几乎恶狠狠地回答:"他一直是个成熟有智慧的孩子,他做的决定我都无条件支持。"他要求最后的日子无论多短,每一日充实度过, 没有遗憾,而不是被困在床上痛苦地捱过去。他的愿望实现了,安东尼在那年秋天安静的去世,被至亲好友围绕,没有太多痛苦。此后阿得有一段很低沉的日子,但是她拒不搬去跟儿女同住。她说自己一辈子依靠自己习惯了,儿女要照顾她,结果只能添乱让她心烦。但是她并不固执,我提议的support group,看心理咨询,她都去了。过了冬,我那时已经换了工作搬到远处,来年跟她通电话时,她说心情已经好多了,又开始戒烟的浩大工程。那一年里发生了许多事,她的大女儿再婚嫁得很好,安东尼自己的女儿也结婚生了孩子,他们一大家子进进出出,离离合合,生老病死。阿得已经有好几个重孙了,她说:我没工夫去理睬他们下一代的事,他们自己去折腾自己的人生吧,我的任务已经完成。
今年我回到本地,约了阿得见面聊天。此时天气已经开始转冷,她见了我时笑笑说:"上礼拜是安东尼去世两周年。"她还象过去一样哇啦哇啦地话多,嘎嘎大笑。宣布计划08年退休,拿了退休金,Medicare,社会保险金,再把房子抵押成reverse mortgage,"我都算好了,钱够用,再无挂心事,我去巴贝朵斯晒晒太阳,在附近做做义工,在附近社区大学选堂课上上。。。"我笑道:"别忘了我老是催你写的回忆录。"跟我解释了半天她是怎么算计各项开支收入之后替自己计划好后路的--"如果一切按照计划实现,我不需要儿女贴补,一切安排地妥妥帖帖直到老死。"我看着她的笑容,叹口气,问道:"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受过高等教育会有怎样的成就。"她想了一想说:"不知道,但是我对这辈子做的所有决定都不后悔。"
"我那时候怀了玛丽亚,一心只盼着逃离那个充满怨恨的家,出来工作养活自己孩子,是我唯一的选择。"我听了脸上不由得红一红--还是根深蒂固的唯有读书高的标准,没了文凭学历,头衔标签,就不知东南西北了。我喜欢听阿得聊天,就是因为她生存在我的世界之外,我在别人铺好的公路上目不斜视地左转右转,从不偏离划好的白线,她在没有路的旷野里赤手空拳独自一人横冲直撞。
她最不耐烦听人说"我不懂","我不会","我不知道"。她告诉我,某同事跟她抱怨说老公在家理财,她担心退休后钱不够用却又无法可想,只有唉声叹气,又怕又担心。阿得把自己收集的各种资料,年金啦,社会保险规定啦,reverse mortgage啦拿来给她看,她瞟了一眼就推开不看说"我不懂,太难了。"阿得厌烦地跟我说:"这种人到处都是,动不动就说我不能。有手有脚,不聋不瞎,肩膀上的脑袋难道是用来摆设的吗?干吗不自己去学?"阿得的胃口很大,对各种事物都有种饥饿的好奇心,她的知识和智慧不是靠书本课堂里教的,而是自己找来自己用,所以没有多余的废话和牛屎,每一样都经过人生的检验。
上次见面,我问阿得作为战后一代在本地长大是怎样的情形和变迁。她说了一些很有见地的话,例如,华盛顿地方的黑人跟南方和中西部不同,"我们没有自卑感。"虽然也有种族主义和隔离政策,本地的黑人比较自信,教育程度和经济地位也比较高,很早就有很多专业人士,艺术和音乐成就,见了白人社会不害怕不退缩,跟美国其他地方不同。又例如,她说民权运动后的混合政策(integration)间接地破坏了黑人社区的繁荣和稳定,因为黑人一旦能够在比较富裕的郊区买房定居,比较中产阶级的家庭就纷纷搬出城里传统的黑人社区,留下的全是贫穷的没有出路的阶层,结果恶性循环,城里本来兴旺繁荣的黑人住宅区和还算好的学校都迅速衰落下去。"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在U街附近有很多剧院和爵士音乐厅。我经常带着女儿去看话剧和歌剧。现在那里天黑了都没人敢出门。"
分别时我说:别忘了,有空写写回忆录,不把你的经历见闻写下来太浪费了。她笑道:等我退了休一定写。
后记:上周忽然收到阿得的一封电邮,告知她的诸位好友相识,不久前她因为贫血去医院看病,结果查出肺癌病灶,所幸是Stage 1,没有转移的迹象,近日便要开刀切除一部分肺。我赶紧打电话给她,家里没人接,打到公司,电话里的声音跟往常一样中气十足。
我惊道:你怎么还在上班?她笑着反问:不上班干什么?我发现肺癌已经快一个月了,等到手术日期定下才宣布的。
我说:你现在心情如何,有人陪吗?她说才不要,虽然儿女都劝她搬过去被照顾,她还是照常独来独往,"家里还有大把琐事要料理呢。"
我叹气:你真勇敢,换了我是你的话早就躲在床底发抖,拖着别人的手一刻也不敢放开。她说她不怕,她的声音里没有一丝恐惧。
我拿着话筒,不知道说什么好。什么样的安慰话俗套话,在这个身经百战的女人面前都苍白无力。两年前我或许会躲在医学技术说法后面,假装镇定自信地说些"一期肺癌应该能治好"的废话,现在我略微少了一点幼稚,而且她肯定把治疗方案,预期prognosis,五年生存机率等等都打听地一清二楚。
"你遗嘱写过了吧?"我问道。我自己想着写遗嘱好几年了都还没动手。
"早写了,还有medical directive, durable power of attorney,早已搞定。"
"可别再抽烟了。"我无力地说。
"我已经一个月没碰烟了。"她愉快地答道。"我下个礼拜五在XX医院开刀,你来看我。"口气就象在说"我要开派对,你来。"
我说好,我一定来。
Last edited by Jun on 2006-11-29 22:29, edited 10 times in total.
-
orangetabby
- Posts: 310
- Joined: 2003-12-06 12:59
-
whyflyaway
- Posts: 4
- Joined: 2006-02-01 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