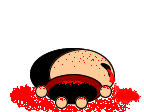外一则:
最近这次买回来的中文书里我最喜欢的是妹尾河童的《窥视印度》,拿起来看第一页就简洁直接,引人入胜。这是我很久以来第一本能让我产生一口气要看到完的冲动的中文书。我对他画的图片不甚感兴趣,这人真是有无穷无尽的童心和耐心,并且态度真诚平易近人,让人读着产生跟他一样产生儿童一般的好奇心。我一口气读到靠结尾处终于开始挑剔,他的丈量瘾让我觉得有点文档的意思了,并且作为一个舞台设计为职业的人,这人对景观的描述基本就是尺寸和颜色,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我以为他的职业怎么也应该算一个文艺界人士,看他写东西倒好像是个工程师。
一个硬币的两面:
看了两页《窥视印度》,我忍不住抓起听说好久,也看了一点点网上做广告的节选的《王蒙自传》,头两页一大堆带“啊”的抒情感叹句,并且隔一段就出现一片排比句抒情,我正处在妹尾河童的干练笔触的引人入胜之中,就非常不耐烦。心想这人怎么写得这么我中学时代的感觉,真老派,大概我现在只喜欢妹尾河童这样现代风格的写作。就扔下了,专心先把《窥视印度》看完。这时候再看《王蒙自传》仍然很不耐烦,他怎么写东西水分这么多,我恨不得把书抓起来拧拧干再看。因为我中学的时候迷过王蒙写新疆的一系列作品,又在高三的时候很摆酷地看了《青春万岁》(,我记得因为那是一本写高三的书,在高三看21岁青年写高三感受的书貌似当年很酷。我们甚至在高三的新年晚会上分几个人朗诵了《青春万岁》的序诗。),王蒙自传第一本正是写这段历史的,我本着8心情坚持像看水分过多的电视连续剧一样快进着给迅速翻完了。第一本里新疆部分很多句子完全出自他当年的小说、散文,这令我很不满。看完这本才知道当年《青春万岁》初稿后寄到人民文学,一年之后有回音,很得赏识但是提出修改意见说是没有主线,作协专门给王蒙当时工作的北京团委发信让王蒙用半年时间专职修改《青春万岁》。(不是这本书的8:据说中国文青一直多,也是由于出版机构有限,人民文学收到的稿子都一麻袋一麻袋的。感想:作协这个单位真是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产物,发信要求人单位给放假写作,估计还是有工资的。原本穷艺术家们在历史的各个阶段都支持性沙龙存在,包括一直到现在的聂华苓和她先生Paul Engle创办的国际作家写作室。8:王蒙当年大概作为文革后很早的一批就去了,蚕的“胡哥”胡续冬刚去了回来。)王蒙花了半年时间给改完了,同时还谈了恋爱。但从此石沉大海,1956年定稿,1979年出书,沉了24年。他自己也发配到新疆做了这么多年右派。在他在新疆做右派期间,他太太带着两个孩子主动调到新疆教书,这期间他们家是他做饭忙家务。(听着有点像李安哦。)一个有潜力的作家从22岁到45岁不让写,也难怪我看他的自传文笔并不比《青春万岁》时好多少,也所以我不满意,但他可以说有他的苦衷。我以为一个自我定位为“作家”的人写自传也应当有文学性,但王蒙就像一个普通北京人一样地白话儿,倒是让人觉得他说得都是真的。王蒙在自传中说:
我就是后来这“平均每三年就要印一次”中的一本的读者。一本书也有自己的命运,原来我并不知道自己当年喜欢的这本书还有这么曲折的经历。这部书(青春万岁)却命运多舛,半个多世纪前,即一九五三年开始写作,一九五六年定稿的这本书,先是打入冷宫近四分之一世纪。一九七九年后才出了书。时过境迁,这本书并没有受到专家们的重视。然而,时至今日,它仍然不断地重印,平均每三年就要印一次,从未间断,前后已经发行了四十多万册,又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了。
在自传第一本,因为有我喜欢过的作品,我看得比较仔细。在众多的水分中过很久会有一些闪亮的句子。比如他回头看侥幸自己在爱情上没有走错路,他说:
又有:二零零四年我在莫斯科看芭蕾舞剧《天鹅湖》,我看到王子受了黑天鹅的迷惑,快要忘记白天鹅奥杰塔的时刻,舞台的背景上出现了一个窗口,是白天鹅的匆忙急迫的舞蹈,这使我回想旧事,热泪盈眶。人生中确实有这样的遭遇,这样的试炼,这样的关口,这样的陷阱。(笑嘻嘻按:看,排比句!)我们都有可能落入陷阱,万劫而不复。这样的故事我就知道不止一个。与真正的所爱告别,与莫名的一位草草成婚,等到想过来,再改变命运谈何容易?闹了一辈子,仍然是错错错,莫莫莫,心比天高,身为下贱,苦想一辈子爱情,最后把自己的情爱搞得臭气熏天... ...有什么办法呢?最最害了自己的往往不是旁人,不是对手,不是敌手,而是你自己。
我这一生常常失误,常常中招,常常轻信而造成许多狼狈。但是毕竟我还算善良,从不有意害人整人,不伤阴德,才得到护佑,在关系一生爱情婚姻的大事上没有陷入苦海。
这两段话我初看非常感动,王蒙的确是一个有思想有性情并且能准确捕捉住这些瞬息想法的人,可是就是对着这些我摘出来的句子,我仍然有抓住拧一拧干的冲动。汉语的平仄四声,抑扬顿挫,句势的罗列反复,论述的大而无当,文字的美轮美奂却无定解,都使阅读与背诵,变得如此快乐迷人控制人,如歌咏如唱赞美诗,如颂咒语如祈祷上苍。
1956年9月《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稿费“四百七十六元”。月薪“八十七元六角四分”。整整六十年代一直到70年最后一批大学毕业生,北京46,部队66,兰州52
何等的感情,何等的脆生。革命胜利的喜悦你会一生重温,你会万年欣然,你会骄傲一代又一代。无怪乎一位台湾背景,定居美国的作家流着泪说,她如果能有机会在那个解放的时刻与大陆人民共享胜利,她此后死了也不冤!还有一位青年评论家说,你们这一代人好赖想着的是革命,我们呢,无事可做了不过打打孩子罢了。当然,他说得不准确,我相信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机遇与局限,但是,这些话的由来,绝非无稽。
这样的激情岁月里有许多难忘的事件。由于乐观和美好预期,鸡蛋曾经降到折合此后的币制一毛钱七八个。一九四九年的北京,确实做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我至今记得,王家英说,毛泽东思想像大海,每个人都可以去舀里边的水,但是水永不枯竭。毛泽东思想像钢琴,每个人都可以用它演奏出无穷的精彩乐章。